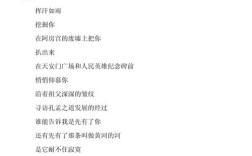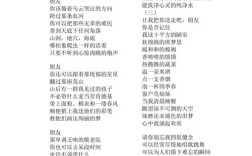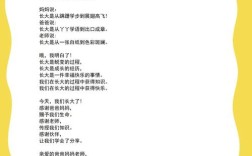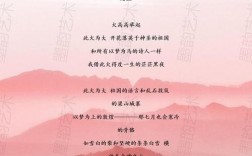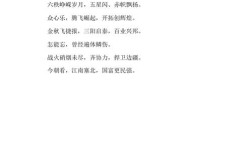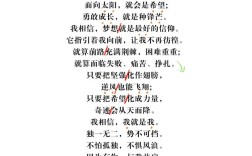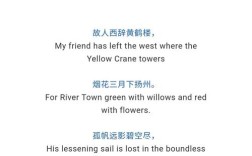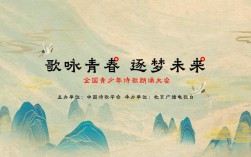诗歌是语言的精魂,是文明长河中不灭的星火,当文字被赋予韵律与情感,便成为穿透时空的桥梁,一场诗歌朗诵比赛,正是让这座桥梁在声音中重生的契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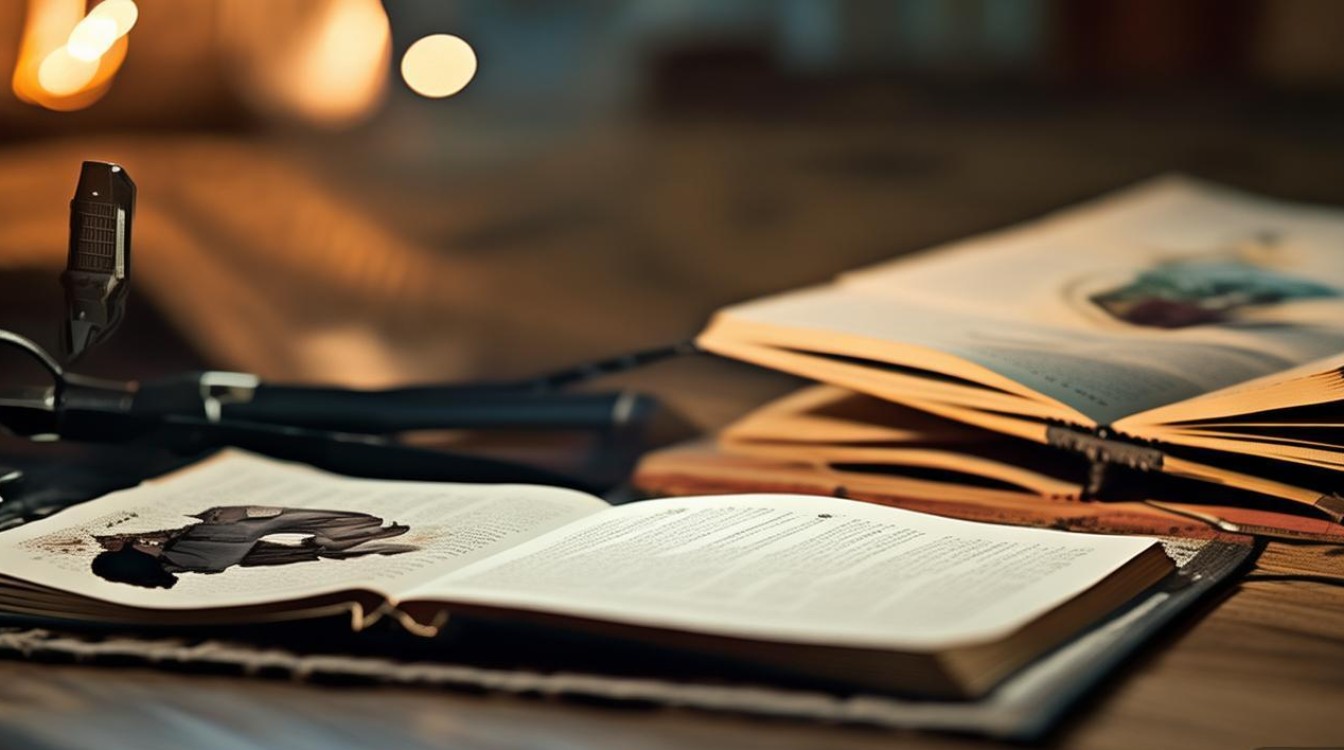
溯源: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诗韵
中国诗歌的源头,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《诗经》。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”的吟唱,不仅是先民生活的写照,更开创了华夏诗歌“赋比兴”的艺术传统,这些来自民间的歌谣,经过孔子整理,成为儒家经典,其凝练的语言、回环的韵律,为后世诗歌奠定了美学基石。
战国时期,屈原在汨罗江畔写下《离骚》。“长太息以掩涕兮,哀民生之多艰”的慨叹,将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熔铸一体,开创了浪漫主义诗歌的先河,楚辞的瑰丽想象与深沉情感,极大地拓展了诗歌的表现疆域。
至唐代,诗歌达到鼎盛,李白的“天生我材必有用,千金散尽还复来”彰显盛唐气象;杜甫的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则承载着士人的忧患意识,这些作品既是诗人个体生命的写照,也是时代精神的结晶。
解构:诗歌创作的匠心独运
理解诗歌的创作背景与手法,是把握其灵魂的关键。
王维的《山居秋暝》写于其隐居蓝田时期。“空山新雨后,天气晚来秋”不仅描绘山水之美,更寄托着诗人超脱尘世的人生理想,这种情景交融的创作手法,使自然景物成为精神境界的外化。
苏轼的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创作于中秋之夜,当时他与弟弟苏辙七年未聚,望月怀人,却能从个人离愁中升华出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的豁达情怀,了解这首词的创作背景,才能深刻体会其中的人生智慧。
诗歌创作讲究意象经营,如马致远《天净沙·秋思》中,“枯藤老树昏鸦”数个意象的叠加,营造出浓郁的羁旅愁思,现代诗歌中,徐志摩的《再别康桥》通过“金柳”“青荇”等意象,将离别之情具象化,这些意象的选择与组合,体现着诗人独特的艺术眼光。
演绎:让诗歌在声音中重生
朗诵是将书面诗歌转化为有声艺术的再创作过程,成功的朗诵需要把握以下几个要点:
首先要深入理解诗歌内涵,朗诵杜甫《春望》时,需体会“国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”中沉痛的家国之忧;演绎李白《将进酒》时,则要把握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的豪迈气势,只有真正读懂诗歌,才能准确传递其情感基调。
其次要注重声音技巧的运用,节奏的控制尤为关键——舒婷《致橡树》的深情需要舒缓的语速,而岳飞《满江红》的激昂则要求铿锵的节奏,音量的强弱变化也能增强表现力,如朗诵戴望舒《雨巷》时,轻柔的声音更能营造朦胧的意境。
语气和停顿的把握同样重要,适当的停顿能制造悬念、突出重点,如在北岛《回答》的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”后稍作停顿,可以强化诗句的批判力量,语气的变化则能生动展现诗歌的情感层次。
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是朗诵的重要辅助,恰当的手势和眼神交流,能够增强诗歌的感染力,但要注意与诗歌内容相协调,避免过度表演。
融汇:古典与现代的对话
当代诗歌朗诵应当打破时空界限,让不同时代的作品在声音中对话,将古典诗词与现代诗歌有机结合,可以展现诗歌艺术的传承与发展。
先朗诵李清照“寻寻觅觅,冷冷清清”的婉约,再接续席慕容《一棵开花的树》的深情,能让听众体会不同时代女性情感的异同;将王之涣“欲穷千里目”的豪情与海子“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”的向往并置,可以引发对人生境界的思考。
这种编排不仅丰富了朗诵的内容层次,更让观众在对比中感受中华诗歌生生不息的艺术魅力。
诗歌朗诵是心灵与心灵的相遇,当声音与诗意交融,每一个音节都成为情感的载体,每一次呼吸都化作理解的桥梁,这不仅是技巧的展示,更是对文化传统的礼敬,在朗诵中,我们不仅再现了诗歌的美学价值,更让千年文脉在当下获得新的生命力,期待在比赛的舞台上,听到属于这个时代的诗音共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