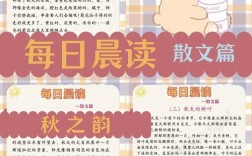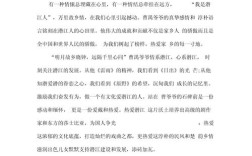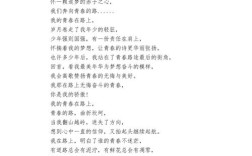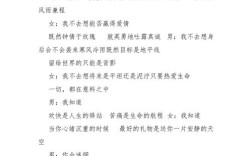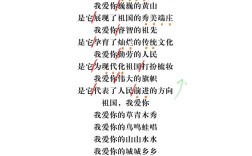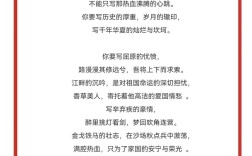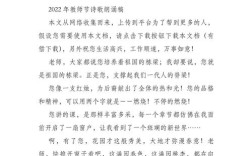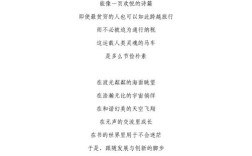诗歌是语言的结晶,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,当千年前的文字依然能触动今人的心弦,我们便知道,诗歌中燃烧着永不熄灭的初心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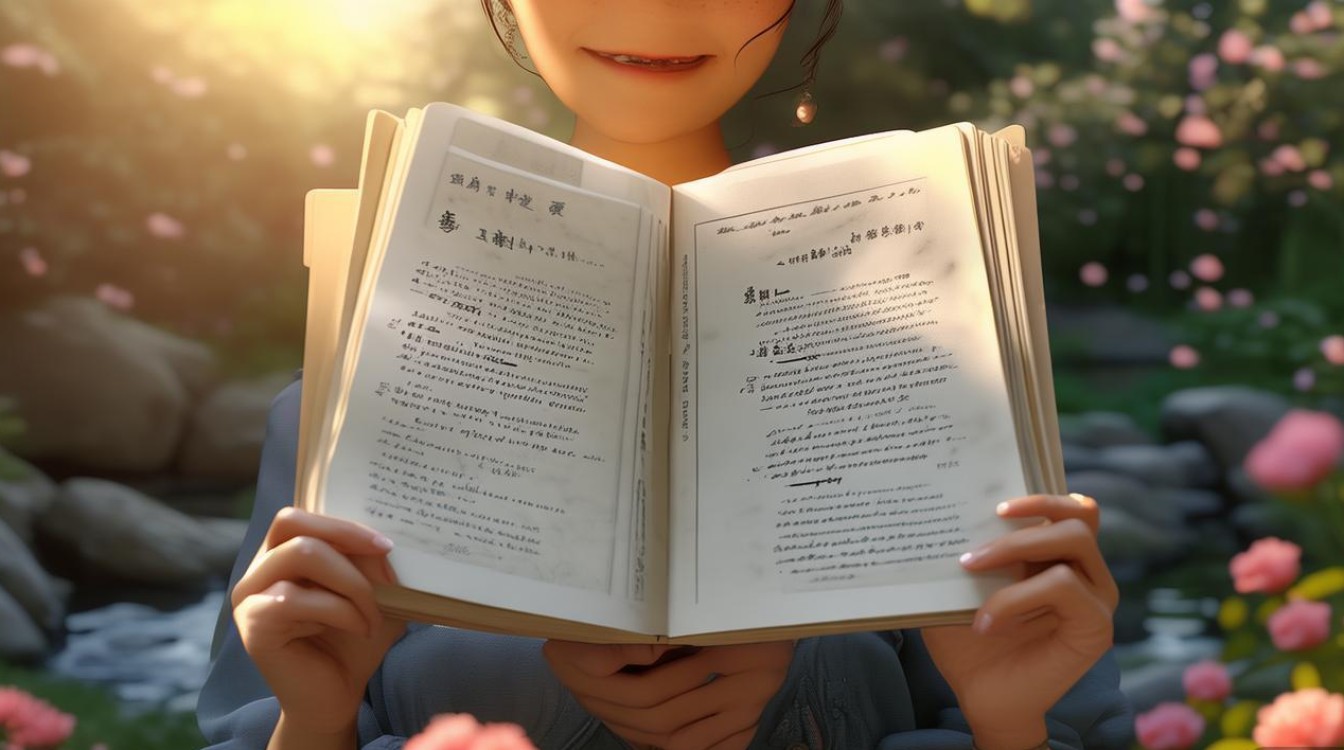
诗词的源流与演变
中国诗歌的源头,可追溯至《诗经》与《楚辞》。《诗经》收录西周至春秋中期的三百零五篇作品,分为“风”“雅”“颂”三类。“风”是各地民谣,“雅”为朝会乐歌,“颂”系祭祀乐章,这些诗歌以四言为主,运用赋比兴手法,开创了中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。
屈原的《楚辞》则开创了浪漫主义先河。《离骚》中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执着,《九歌》中湘君湘夫人的缠绵,都展现了与《诗经》不同的艺术风貌。
汉乐府继承《诗经》传统,“感于哀乐,缘事而发”。《孔雀东南飞》的悲剧、《上邪》的誓言,都是鲜活的时代记录,魏晋时期,五言诗成熟,曹操《短歌行》的慷慨、陶渊明田园诗的恬淡,各具特色。
至唐代,诗歌达到鼎盛,初唐四杰奠定格律诗基础;盛唐李白杜甫并称“李杜”,一个豪放飘逸,一个沉郁顿挫;中唐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;晚唐李商隐深情绵邈,宋词继唐诗后成为又一高峰,苏轼辛弃疾的豪放、柳永李清照的婉约,共同构筑了宋词的艺术殿堂。
诗人与时代的对话
理解诗歌,必须了解诗人与其时代的关系,杜甫被尊为“诗圣”,其作品被称为“诗史”,正因他的诗歌深刻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。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不仅是诗句,更是时代的控诉。
李商隐的《无题》诗向来难解,“相见时难别亦难,东风无力百花残”的朦胧,与其身处牛李党争的处境密切相关,诗人将难以言说的情感寄托在意象中,创造了独特的艺术境界。
苏轼的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写于中秋之夜,当时他外放密州,与弟弟苏辙七年未聚。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”既是对弟弟的思念,也是经历“乌台诗案”后的人生感悟。
诗歌的表现艺术
诗歌艺术的核心在于意象与意境的营造,意象是融入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,马致远的《天净沙·秋思》中,“枯藤老树昏鸦,小桥流水人家”连续多个意象组合,营造出浓郁的羁旅愁思。
意境则是意象构成的整体艺术境界,王维的山水诗最具代表性,“空山新雨后,天气晚来秋”不只是景物描写,更创造出物我两忘的禅意境界。
诗歌的表达手法丰富多彩,比喻使抽象具体化,李煜将愁绪比作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;象征赋予物象深层含义,于谦以“粉身碎骨全不怕,要留清白在人间”的石灰自喻;用典借古喻今,辛弃疾词中典故层出,增加了历史厚重感。
对仗和平仄是古典诗词形式美的重要元素,杜甫“两个黄鹂鸣翠柳,一行白鹭上青天”,数字对数字,颜色对颜色,名词对名词,工整而不呆板。
诗词的现代价值
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,诗歌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,读诗是培养语言敏感度的最佳途径,当我们反复品味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的“绿”字,就能体会古人“吟安一个字,捻断数茎须”的苦心。
诗歌创作可以成为现代人的精神栖息地,不必拘泥于严格的格律,从观察生活、记录感受开始,用简洁凝练的语言表达真情实感,就是诗歌精神的延续。
将诗歌融入生活,晨起读一首王维,感受“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”的宁静;夜晚吟一阕苏轼,体会“人生如梦,一尊还酹江月”的旷达,诗歌不是束之高阁的文物,而是随时可以对话的朋友。
诗歌教育应当重视感悟而非死记硬背,带孩子走进自然,观察“细雨鱼儿出,微风燕子斜”的生动;引导他们体会“桃花潭水深千尺,不及汪伦送我情”的友谊,当诗歌与生活经验结合,就会在心灵中生根发芽。
诗歌是文明的火种,代代相传,每一次诵读,都是与古人的握手;每一次创作,都是初心的点燃,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,我们更需要诗歌来守护内心的宁静,在平仄起伏中寻找精神的归宿,在千年韵律里确认文化的认同,让诗歌的火焰永不熄灭,照亮每个寻找美与真理的心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