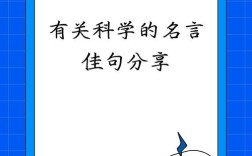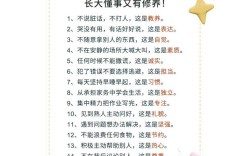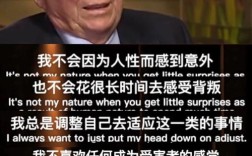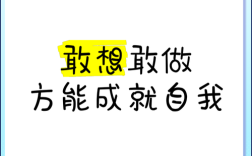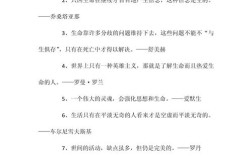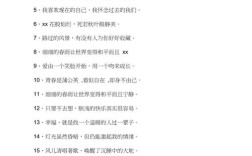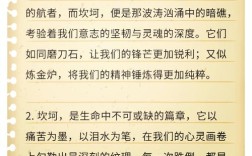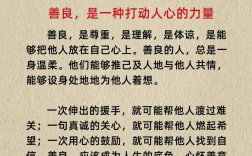关于唤醒与希望
这些名言表达了作者创作的初衷——希望用文字唤醒沉睡的国人,在绝望中寻找希望。

“从来如此,便对么?”
- 出处:《狂人日记》
- 解读:这是《呐喊》开篇之作《狂人日记》中的一句石破天惊的诘问,它挑战了根深蒂固的传统和陈规,要求人们对习以为常的事物进行独立的思考和批判,这句话体现了鲁迅“五四”时期反封建、反传统的核心精神,是思想启蒙的号角。
“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,然而说到希望,却是不能抹杀的,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,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,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,……。”
- 出处:《故乡》
- 解读:在《故乡》的结尾,鲁迅在表达了对现实的失望后,依然对未来抱有审慎的希望,他认为希望本是无所谓有,无所谓无的,这正如地上的路;其实地上本没有路,走的人多了,也便成了路,这句话充满了辩证法的智慧,强调主观能动性,鼓励人们去开辟新的道路。
“假如一间铁屋子,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,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,不久都要闷死了,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,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,现在你大嚷起来,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,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,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?”
- 出处:《〈呐喊〉自序》
- 解读:这是钱玄同与鲁迅的一段对话,是理解《呐喊》创作动机的关键,鲁迅将当时的中国比作“铁屋子”,将民众比作“熟睡的人”,他最初对“呐喊”能否唤醒众人并让他们承受清醒的痛苦感到犹豫,但最终,他还是选择了呐喊,因为即使只能惊醒几个人,让他们感受到痛苦,也比在沉默中死去要好,这体现了鲁迅作为启蒙者的责任感与牺牲精神。
关于国民性与麻木
这些名言深刻地剖析了当时中国民众的精神状态,尤其是麻木、愚昧和看客心理。
“我翻开历史一查,这历史没有年代,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‘仁义道德’几个字,我横竖睡不着,仔细看了半夜,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,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‘吃人’!”
- 出处:《狂人日记》
- 解读:这是《狂人日记》的点睛之笔,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最经典的句子之一,鲁迅以“狂人”的视角,撕开了封建礼教温情脉脉的面纱,直指其“吃人”的本质,这里的“吃人”不仅指肉体上的吞噬,更指精神上的压迫、对人性的扼杀和个体的消亡。
“凡是愚弱的国民,即使体格如何健全,如何茁壮,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,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,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,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。”
- 出处:《〈呐喊〉自序》
- 解读:这是鲁迅弃医从文的根本原因,他在日本仙台学医时,从看客们的麻木神情中认识到,疗救精神比疗救肉体更为重要,一个民族如果精神上病了,那么强健的体魄也只是示众的材料,他决心用文艺来改变国民的精神。
“阿Q不独是姓名籍贯有些渺茫,而且连他先前的‘行状’也渺茫。”
- 出处:《阿Q正传》
- 解读:这句看似平淡的叙述,却揭示了阿Q这个人物的悲剧性,他失去了自我,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,只能通过“精神胜利法”来麻痹自己,这句引语开启了鲁迅对阿Q这个“国民劣根性”集合体的深刻刻画。
“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。”
- 出处:《孔乙己》
- 解读:这是《孔乙己》的结尾,一个看似矛盾的句子。“大约”是因为没有人关心他的死活,没人能确定;“的确”是因为在那样冷漠的社会环境下,他除了死亡别无出路,这句话充满了悲凉,揭示了社会对底层知识分子的漠视与摧残。
关于批判与反思
这些名言直接指向了社会现实,充满了批判精神和深刻的反思。
“我懂得他的意思了,他们快要结婚之前,本来已经有过一次血光之灾,一个死掉了,这回不应该再到那里去,倘去了,就会有第二次的。”
- 出处:《药》
- 解读:这是小说《药》中的一个情节,华大妈在坟地与夏四奶奶的对话,这里的“血光之灾”和“死掉”指的是革命者夏瑜被杀害,民众不仅不理解革命,反而将革命者的鲜血当作治病的“药引子”,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革命与民众的严重脱节,以及群众的愚昧和麻木。
“他只是摇头,脸上虽然窘苦,却嬉笑的神情。”
- 出处:《孔乙己》
- 解读:这是对孔乙己的经典描写,即使在被众人嘲笑、生活困窘到极点时,他依然用“嬉笑”来掩饰自己的痛苦和尊严的丧失,这既是他个人的悲剧,也是那个时代无数知识分子的缩影。
“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,我以为在这途路中,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。”
- 出处:《〈呐喊〉自序》
- 解读:这是鲁迅对自己人生经历的总结,他从家道中落中感受到了世态炎凉和人情的冷暖,看透了社会虚伪的“真面目”,这种切肤之痛,成为他深刻批判社会现实的重要动力。
鲁迅的《呐喊》之所以不朽,正是因为这些名言超越了时代,直指人心,它们不仅是对旧中国社会的诊断书,更是对人性弱点的深刻洞察,至今,这些文字依然像警钟一样,提醒我们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,敢于质疑,勇于反思,并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“呐喊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