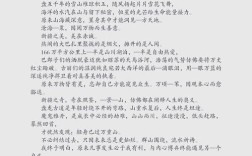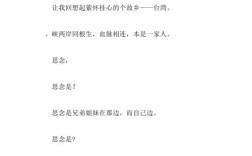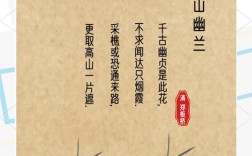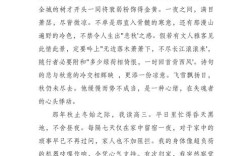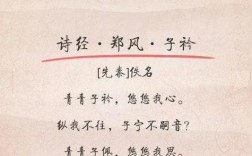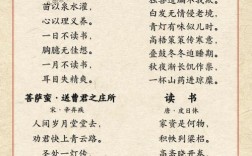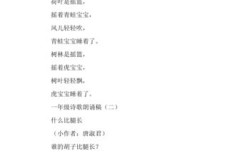诗歌,是人类情感最凝练的结晶,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,当我们将某首诗、某句词视为精神世界的“唯一”时,它便不再仅仅是文字的组合,而成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灯塔,要真正理解并珍视这份“唯一”,我们需要走进它的世界,了解它的来龙去脉与表达艺术。
溯源:认识诗歌的“身世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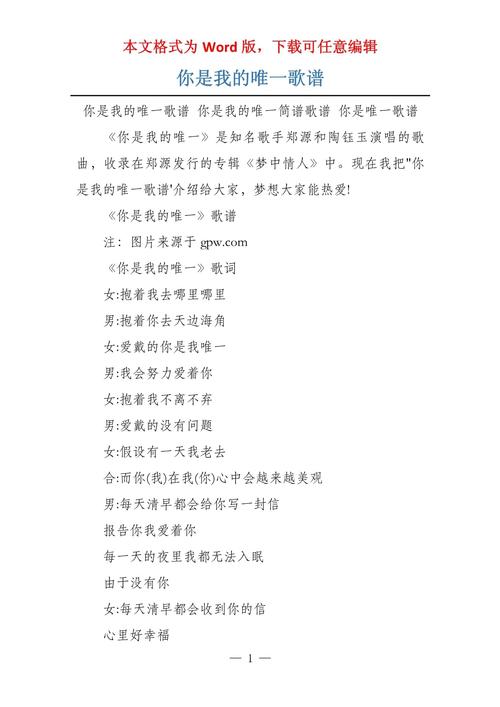
一首诗能成为“唯一”,首先源于其独特的“身世”,这包括它的出处、作者与创作背景,三者共同构成了诗歌的根基。
出处,即诗歌的载体与流传,它可能源自一部诗集,如《全唐诗》、《宋词三百首》;也可能记录于某部史书或笔记,如《史记》中的《垓下歌》;或是镌刻在山水之间的碑文题壁,了解出处,能帮助我们判断文本的可靠性,并感知其最初被传播的语境,一首收录于官方编纂诗集的作品,与一首通过民间歌谣传唱的作品,其气质与风格往往迥异。
作者,是诗歌的灵魂赋予者,了解作者的生平、思想、主要成就与人生阶段,是解读诗歌的钥匙,李白的浪漫飘逸与杜甫的沉郁顿挫,根源在于他们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与性格,知道苏轼历经“乌台诗案”后的心境变化,才能更深切地体会《定风波·莫听穿林打叶声》中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旷达与坚韧,作者的人格魅力与思想深度,常常是诗歌打动人心的核心力量。
创作背景,是诗歌诞生的具体时空与情境,这包括时代背景(如盛唐的开放、南宋的偏安)、具体事件(如送别、登高、国破家亡)以及作者当下的心境,王维的《使至塞上》,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的壮美,离不开他奉命赴边塞慰问将士的特定行程与见闻,李清照的《声声慢·寻寻觅觅》,那彻骨的凄冷与哀愁,与她晚年国破家亡、流离失所的境遇密不可分,背景为诗歌提供了最真实的注脚,让抽象的情感变得具体可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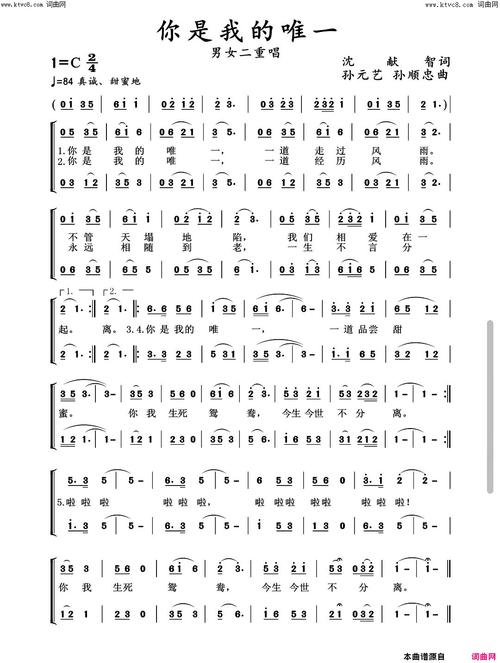
品鉴:领悟诗歌的“表达艺术”
理解了诗歌的“身世”,我们还需掌握品鉴其美感的方法与手法,才能完全领略其作为“唯一”的艺术魅力。
使用方法,这里指我们接近诗歌的途径,首先是反复吟诵,诗歌的节奏、音韵、平仄之美,唯有通过出声朗读才能充分体会,其次是意象捕捉,诗歌很少直白抒情,而是通过“意象”(如明月、杨柳、孤舟、落花)的组合来营造意境、传递情感,试着找出诗中的核心意象,并感受它们构成的画面与氛围,最后是情感共鸣,将自身经历与诗歌情感相联系,进行个性化解读,是诗歌成为“唯一”的关键一步。
使用手法,即诗歌创作中运用的具体艺术技巧,掌握一些基本手法,能极大提升鉴赏的深度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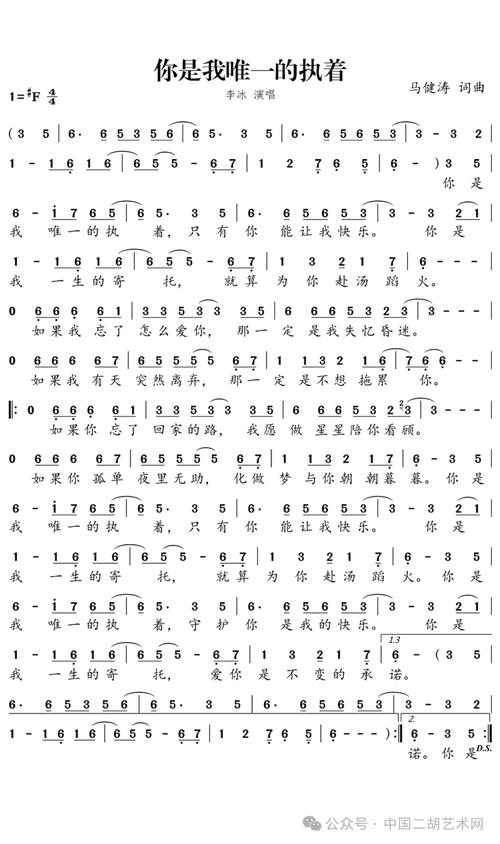
- 赋、比、兴:这是中国诗歌的源头性手法。“赋”是直陈其事,如“迢迢牵牛星,皎皎河汉女”;“比”是比喻,如“问君能有几多愁?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;“兴”是由物起兴,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,如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”引出“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”。
- 象征与用典:象征是用具体事物代表抽象概念,如“松竹梅”象征高洁品格,用典是引用历史故事或前人诗句,以简驭繁,丰富内涵,如辛弃疾词中大量运用历史典故来表达复国壮志。
- 虚实结合:实写眼前景、当下事,虚写想象、回忆或梦境,二者结合,拓宽了诗歌的时空与意境,如李商隐“何当共剪西窗烛,却话巴山夜雨时”,由实景生发虚想,情感更深婉。
- 对比与烘托:通过对比强化效果,如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;通过环境描写烘托人物心情,如“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日看尽长安花”。
- 语言的锤炼:关注“诗眼”或词中精妙字句,王安石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的“绿”字,贾岛“僧敲月下门”的“敲”字,都是反复锤炼、化平常为神奇的典范。
内化:让诗歌成为生命的“唯一”
当我们对一首诗的身世与艺术有了深入了解后,它与我们的关系便开始深化,它可能在某个人生节点精准地击中了我们的心灵,其表达成为我们情感的代言;它的哲理为我们提供了看待世界的独特视角;它的美感滋养了我们的审美趣味,这时,诗歌便从公共的文化遗产,转变为个人精神世界不可替代的“唯一”。
这个过程需要主动的投入,可以尝试创作,哪怕只是模仿句式与意境,也能更深切地体会创作的甘苦与表达的精确,可以围绕喜爱的诗歌进行扩展阅读,了解相关评论、不同解读,甚至与之相关的音乐、绘画作品,构建一个以这首诗歌为核心的小小知识体系。
诗歌作为“唯一”,其价值不在于束之高阁的崇拜,而在于日常的浸润与对话,它是在迷茫时给予方向的光,是在孤独时默默陪伴的友,是在欢欣时能够共享的知己,每一首能触动你的诗歌,都为你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,丰富了你生命的维度。
真正热爱诗歌,便是愿意花费时间去了解它的故事,揣摩它的字句,感受它的心跳,最终让它融入自己的血脉,成为精神家园里最独特、最明亮的那颗星,这份“唯一”,是知识与情感共同作用的成果,是跨越千年依然鲜活的生命力所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