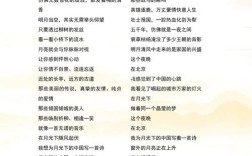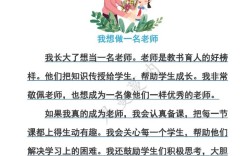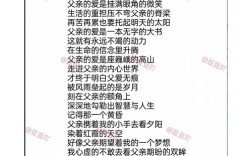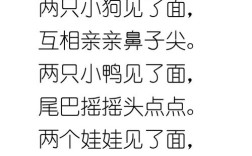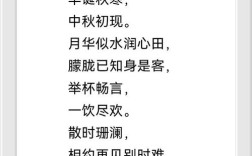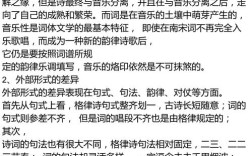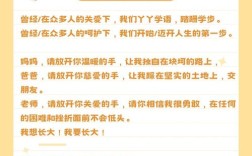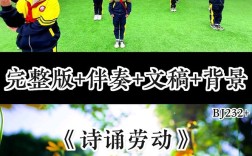大唐诗歌,宛若一座巍峨壮丽的文化高峰,矗立于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,它不仅是一个时代的文学结晶,更是千年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璀璨映射,理解这些诗篇,需要我们穿越时空,走进那个气象万千的时代,探寻文字之外更为深广的意境。

要真正读懂一首唐诗,首先要回到它的创作现场,诗歌并非孤立存在的文字游戏,而是诗人生命体验与时代风云交织的产物,李白的《早发白帝城》中,“朝辞白帝彩云间,千里江陵一日还”的豪迈,若不置于诗人遇赦东归的特定背景之下,便难以体会字里行间那种重获自由的轻快与激昂,同样,杜甫的“国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”,若脱离了安史之乱后长安沦陷的历史图景,便无法感受其中沉郁顿挫的家国之痛,每一首经典诗作都像一扇窗,透过它,我们得以窥见唐代社会的政治生态、文化风尚与文人心境。
了解诗人的生平际遇,是解锁其作品内涵的另一把钥匙,唐代诗人群体构成多元,从宫廷贵族到边塞将士,从隐逸山人到落魄文人,不同的生命轨迹塑造了各自独特的诗歌风格,王维中年后笃信佛教,半官半隐于辋川别业,笔下才有“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”这般空灵禅意的境界,高适、岑参等人长期生活在边疆要塞,他们的边塞诗便充满了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的雄浑苍茫,诗人的个人气质、仕途浮沉、交游经历,无不深深烙印在字句之间,成为我们解读诗歌的情感密码。
在创作技法上,唐诗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巅峰,格律的严谨与意境的营造相得益彰,形成了一套极为精妙的表达体系,近体诗对平仄、对仗、押韵的规范,非但没有束缚诗人的才情,反而在限制中激发出更大的创造力,以杜甫《登高》为例,“风急天高猿啸哀,渚清沙白鸟飞回”,字字对仗工整,音韵铿锵,却自然流畅,毫无斧凿之痕,诗人还善用比兴手法,托物言志,借景抒情,李商隐的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”,表面写物,实则寄托着至死不渝的思念,这种含蓄蕴藉的表达方式,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审美层次。
将这些千年诗魂融入当代生活,能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,在个人修养层面,唐诗是陶冶性情、提升审美能力的绝佳载体,反复吟咏王勃的“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”,可以培养豁达的胸襟;品味李白的“天生我材必有用,千金散尽还复来”,能够建立自信乐观的人生态度,在文学创作中,唐诗的意象、句法、修辞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,适当化用能为现代文章增添古典韵味,柳宗元“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的孤高形象,至今仍是文学艺术中常用的精神符号。
从更广阔的视角看,唐诗的价值早已超越文学本身,成为构建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资源,这些诗篇记录了我们祖先对自然、社会、人生的深刻思考,承载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情感表达方式和价值观念,无论是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的进取精神,还是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的济世情怀,都是中华文明精神谱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,在全球化语境下,唐诗作为中国文化“走出去”的亮丽名片,正以其普世的情感价值和独特的艺术魅力,架起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。
面对这样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,我们的学习不应停留在机械背诵的表层,真正理解唐诗,需要放下功利心态,以从容的心境去贴近那些伟大的灵魂,不妨在一个安静的午后,泡一杯清茶,轻声诵读杜牧的《秋夕》:“银烛秋光冷画屏,轻罗小扇扑流萤。”让思绪随着诗句的节奏,慢慢沉浸到那个遥远而美好的秋夜之中,这种跨越千年的心灵对话,或许正是唐诗永恒魅力的最好证明。
唐诗的世界浩瀚无垠,每一次深入都是一次精神的洗礼,这些经过时间淬炼的文字瑰宝,不仅属于那个已经远去的盛世,更属于每一个愿意用心聆听的现代人,在这个变化莫测的时代,唐诗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恒定的文化坐标,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,依然能找到精神的归宿和情感的共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