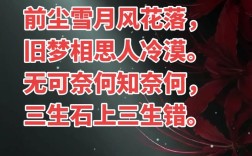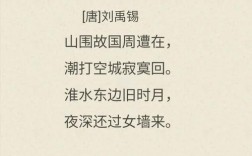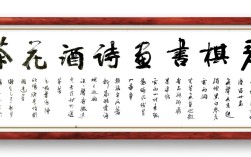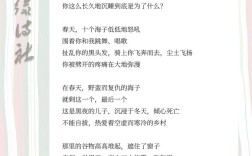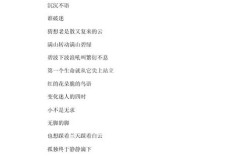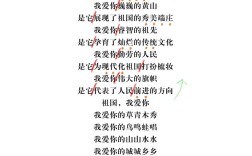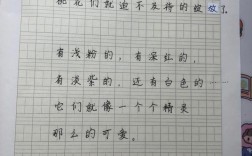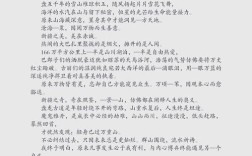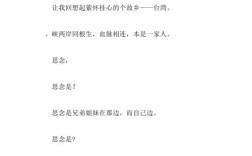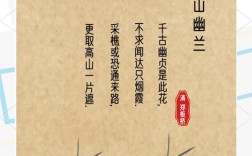窗花与诗词,恰似红纸与墨痕的交织,一剪一刻间勾勒出千年文化的魂魄,当剪刀游走于丹红宣纸,诗句便从镂空的纹样里流淌出来,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最灵动的注脚。

民间智慧与文人雅趣的合流
剪窗花习俗可追溯至汉代造纸术普及时期,而将剪纸艺术与诗歌相融合的记载最早见于唐代,李商隐在《人日即事》中写下“镂金作胜传荆俗,剪彩为人起晋风”,证实当时已存在将剪纸与节令仪式结合的成熟传统,宋代《武林旧事》记载立春时节“街市以花装栏,坐乘小春牛,及春幡春胜皆系镂金纸为之”,这些金箔剪纸常题写吉庆诗句,成为诗与剪影的早期共生形态。
明清时期达到鼎盛,文人开始专门为窗花创作题诗,郑板桥在题《剪纸》诗中描绘:“剪碎月华光满地,玲珑巧作报春图”,既记录剪纸工艺的精妙,又赋予其诗意解读,这类作品往往采用竹枝词形制,语言通俗却意境深远,成为连接士大夫文化与民间艺术的重要桥梁。
创作技法的诗性转化
传统窗花诗歌的创作核心在于“意象转译”,匠人需将剪纸的视觉元素转化为诗歌语汇,如将“鱼戏莲叶”图式转化为“莲动知鱼乐”的意境,将“喜鹊登梅”转化为“梅梢春信近”的期待,这种转译要求作者同时精通两种艺术形式的符号系统。
在格律运用上,窗花诗多采用七绝或五古体,七绝的紧凑结构适合表现窗花的精巧构图,如清代佚名《咏剪纸》:“方寸玲珑百态生,春风先上纸边轻,不须更染丹青色,自有梅花暗香盈。”方寸玲珑”对应剪纸的尺幅限制,“纸边轻”暗喻剪纸的轻薄特质,最后以通感手法将视觉转化为嗅觉,完成艺术维度的跃升。
地域流变中的诗意表达
北方窗花诗风格刚健明快,河北蔚县剪纸传承人王老赏的题诗:“三刀剪出牡丹红,五更灯火映雪明”,直接展现创作场景,动词运用极具力度,而南方以上海为代表的都市窗花诗则更显婉约,如海上画派画家任伯年题《申江剪彩图》:“吴绫剪作流云纹,半入江风半入云”,将剪纸与自然景象交融,体现文人化的审美倾向。
少数民族地区同样存在独特的窗花诗传统,大理白族剪纸常配“玉洱银苍”题材的“山花体”诗歌,采用三七一五句式,如“心似剪纸样样明/红线白纸总关情/金花要配银线绣/蝴蝶飞来不成双”,将民族情感与手艺传承紧密结合。
当代创作的诗学拓展
现代窗花诗歌在继承传统基础上进行多重创新,诗人林庚的《剪纸》开创象征主义路径:“无数个春天在剪刀下/绽放成透明的预言”,将剪纸提升为生命哲学的载体,手艺人也开始自觉进行诗歌创作,陕西剪纸非遗传承人库淑兰的自创诗:“剪花娘子把花剪,剪出日月放光芒”,用质朴语言构建民间叙事体系。
在数字化时代,窗花诗歌衍生出交互式创作,中央美院开展的“数字剪纸诗”项目,通过算法将诗句实时转化为剪纸图案,如输入“云破月来花弄影”,程序即生成对应镂空纹样,实现传统技艺与人工智能的对话。
鉴赏要诀与创作门径
鉴赏窗花诗歌需把握三个维度:首先是“形意契合度”,观察图案与诗句的意象呼应是否精妙;其次是“时空穿透力”,优秀作品应同时体现历史厚度与当代意识;最后是“工艺文学性”,通过刀法痕迹解读诗意表达,如断续的剪口可能暗示诗句中的留白意境。
初学者创作可从三方面入手:选取经典窗花纹样进行仿写训练,如针对“连年有余”图案练习对仗句式;掌握剪纸术语的诗化表达,将“阳刻”转化为“留白守黑”,“阴刻”喻指“虚怀若谷”;注重节令特征的融入,立春题材可化用“东风解冻”典故,中秋主题则可呼应“团圆剪影”传统。
这种承载千年手艺的诗歌形态,始终在剪刀与笔墨的碰撞中生长,当指尖抚过诗行间的镂空痕迹,便能触碰到中国人将日常生活转化为永恒诗意的独特智慧,在机械复制的时代,窗花诗歌提醒着我们:真正的创造永远始于心灵与双手的对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