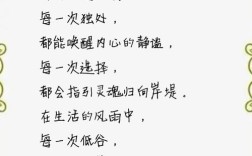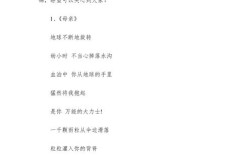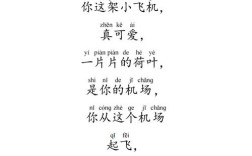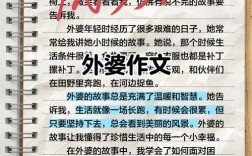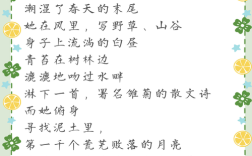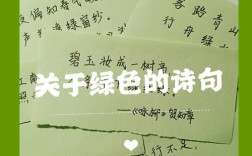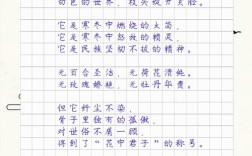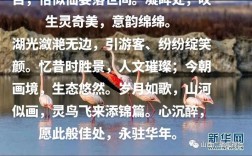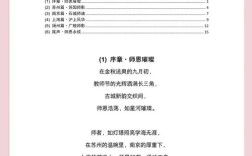悲伤诗歌如同一面镜子,映照出人类共有的情感脉络,这些凝结着泪水的文字,跨越时空界限,构建起连接古今的桥梁,当我们沉浸于这些诗句时,不仅能感受到作者彼时的心境,更能从中照见自己的灵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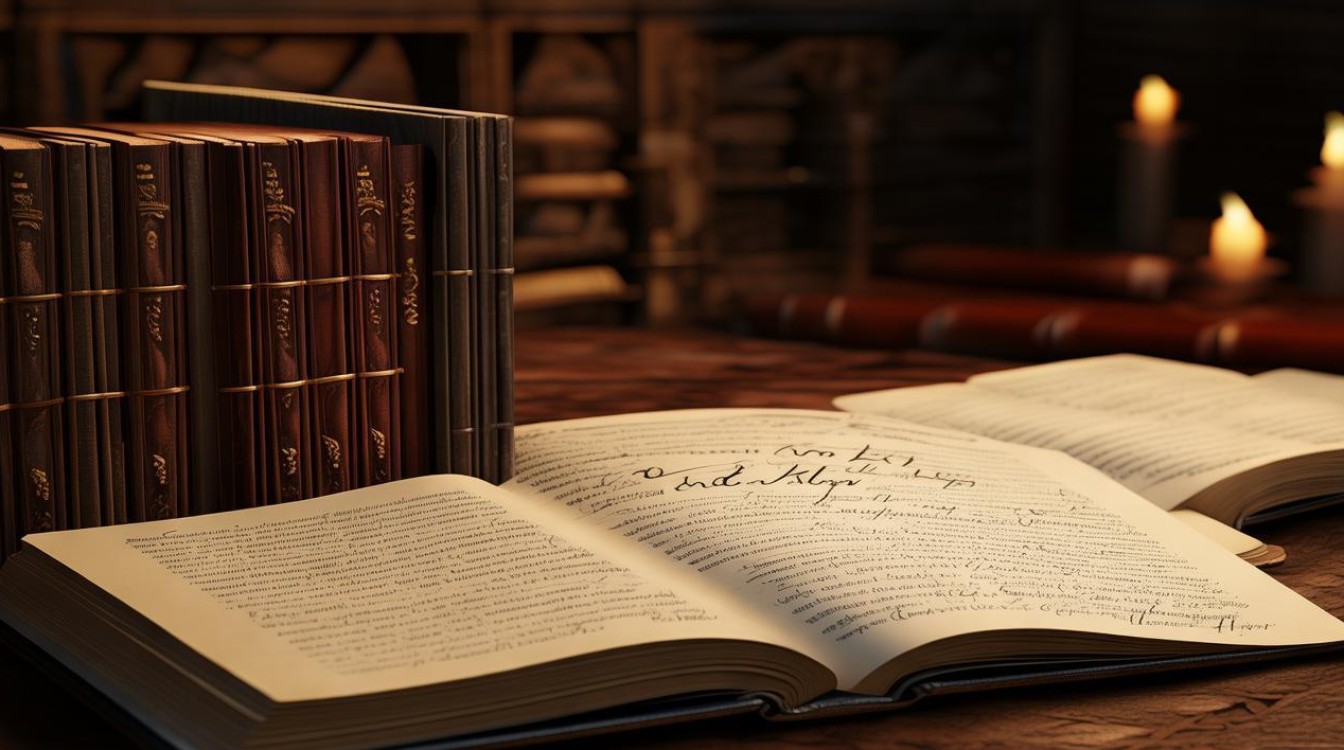
古典悲诗的源流与演变
《诗经》中《小雅·采薇》的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,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”,以简练笔触勾勒出征人归乡的复杂心绪,四句诗中不见“悲”字,却通过自然景物的对比,将岁月流逝、物是人非的苍凉感表现得淋漓尽致,这种含蓄蕴藉的表达方式,成为中国古典诗歌悲情书写的重要传统。
屈原在《离骚》中开创了以香草美人喻君臣关系的悲情表达。“长太息以掩涕兮,哀民生之多艰”,诗人将个人政治失意的悲痛与对民生的关切融为一体,提升了悲伤诗歌的思想高度,这种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相结合的创作理念,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建安时期,曹操的《蒿里行》以“白骨露于野,千里无鸡鸣”描绘了战乱后的凄惨景象,诗歌中的悲悯不再局限于个人际遇,而是扩展至对百姓命运的深切关怀,这种现实主义的悲歌,为悲伤诗歌注入了深厚的社会内涵。
唐代杜甫的《春望》中,“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”以拟人手法赋予自然景物以情感,将国破家亡的痛楚与自然景象相融合,这种移情于物的表现手法,使得悲伤情绪的传达更为深刻动人。
李商隐的《锦瑟》以“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”道出了对往昔的追忆与怅惘,诗中运用大量典故与象征,营造出朦胧凄美的意境,展现了晚唐诗歌特有的感伤美学。
诗歌创作技巧解析
意象选择在悲伤诗歌中占据核心地位,李煜《虞美人》中“问君能有几多愁,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,以滚滚东流的江水比喻愁绪,将抽象情感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,这种意象营造手法,使读者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情感的强度与绵延。
对比手法能强化悲伤的表达效果,苏轼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》中“十年生死两茫茫,不思量,自难忘”,通过生死相隔的对比,凸显出对亡妻刻骨铭心的思念,时间与空间的阻隔,反而使得情感更为浓烈。
细节描写往往能触动人心最柔软的部分,陆游《沈园二首》中“伤心桥下春波绿,曾是惊鸿照影来”,通过对旧地重游时特定景物的细致描绘,唤起了对往昔美好时光的回忆,这种以小见大的笔法,让悲伤情绪有了具体的附着点。
用典技巧能增加诗歌的历史厚重感,辛弃疾《摸鱼儿》中“君莫舞,君不见、玉环飞燕皆尘土”,借历史人物的命运抒发现实感慨,典故的恰当运用,使得个人的悲伤与历史长河中无数相似命运产生共鸣。
诗歌鉴赏与情感共鸣
理解诗歌创作背景是深入把握作品情感的关键,李清照《声声慢》中“寻寻觅觅,冷冷清清,凄凄惨惨戚戚”,若不了解词人历经国破家亡、流离失所的人生经历,便难以体会这七组叠字所蕴含的深重悲苦。
把握诗歌的情感层次能提升鉴赏深度,白居易《长恨歌》既描写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,也隐含了对王朝兴衰的感慨,这种多重情感的交织,使得诗歌具有更为丰富的阐释空间。
注意诗歌中的情感转折往往能发现作者的深意,李商隐《夜雨寄北》中“何当共剪西窗烛,却话巴山夜雨时”,从当前孤寂的雨夜景象,转而想象未来重逢的温馨场景,这一转折非但没有冲淡思念之情,反而通过虚实相生的笔法,强化了当下处境的凄凉。
现代语境下的诗歌应用
在文学创作中,古典悲伤诗歌的意境与技巧仍具借鉴价值,许多现代诗人从古典诗歌中汲取营养,将传统悲情表达与现代语言相结合,创作出既有古典韵味又具时代特色的作品。
在情感教育方面,悲伤诗歌能帮助人们理解并接纳负面情绪,通过阅读这些作品,读者能够认识到悲伤是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,从而更好地处理自己的情绪波动。
在审美培养过程中,欣赏悲伤诗歌有助于提升对美的多元认知,悲情作为一种审美范畴,其价值不在于消极情绪的宣泄,而在于通过艺术化的表达,使痛苦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学体验。
在文化交流领域,悲伤诗歌成为沟通不同文化的桥梁,由于人类情感的相通性,表达悲情的诗歌往往能够超越语言与文化的障碍,引起不同背景读者的共鸣。
悲伤诗歌的价值不仅在于其艺术成就,更在于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生命、面对苦难的智慧,每一首流传至今的悲伤诗歌,都是前人情感与智慧的结晶,在这些诗行间,我们既能找到情感的慰藉,也能获得精神的启迪,真正理解这些诗歌,需要的不仅是文学素养,更是对生命本质的深刻体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