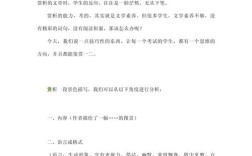漫步于古典诗歌的长廊,景语是叩开诗人心扉的第一道门扉,山川草木,风霜雨雪,在诗人的笔端不仅是自然存在,更是情感与哲思的载体,学会鉴赏诗歌中的景物形象,便是掌握了一把解读千年诗心的钥匙。
溯本清源:景物形象的出处与作者心迹

诗歌中的景物,绝非凭空虚构,其出处往往紧密联结着诗人的生命轨迹与地理空间,王维笔下“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”的幽静,源自其辋川别业的实景与长期半官半隐的生活体验;岑参诗中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瑰奇边塞雪景,则直接诞生于其远赴安西、北庭的独特军旅历程,了解景物形象的出处,实质是在确认诗歌情感的地理坐标。
更进一步,同一景物在不同诗人眼中,会折射出迥异的光彩,同是登高望远,杜甫在《登高》中看到的是“无边落木萧萧下,不尽长江滚滚来”,沉郁顿挫中饱含家国之忧与身世之悲;而王之涣在《登鹳雀楼》中吟出“白日依山尽,黄河入海流”,则展现出盛唐时代开阔进取的胸襟气度,景物如同镜鉴,清晰映照出作者各异的人生境遇、性格气质与时代精神,鉴赏时首要之务,是将景物放回其诞生的具体土壤——诗人的生平与时代中去理解。
知人论世:创作背景赋予景物深度
创作背景是理解景物形象深层意蕴的枢纽,它如同调色盘,决定了景物呈现的情感基调,李白的《早发白帝城》,“朝辞白帝彩云间,千里江陵一日还”,笔下的三峡江水迅疾轻快,两岸猿声也显得亲切,若不联系其创作背景——流放途中忽遇赦免,乘舟东归——便难以全然体会这明丽景物中喷薄而出的狂喜与畅快。

相反,姜夔《扬州慢》中的“过春风十里,尽荠麦青青”,昔日繁华的扬州道上,只见一片青青野麦,荒凉破败的景物背后,是词人对金兵蹂躏后城池残败的深沉哀恸,是南宋国势衰微的缩影,时代的风云变幻、个人的荣辱得失,都会沉淀为景物描写的底色,脱离背景,景物便易沦为单薄的画面;结合背景,方能触摸到形象之下涌动的历史温度与生命感慨。
细察笔法:塑造景物形象的艺术手段
诗人如何将眼中之景转化为诗中之意象?这离不开精妙的艺术手法。
多种感官的交融互通,王维堪称此中圣手,“泉声咽危石,日色冷青松”,不仅有色(日色、青松),更有声(咽咽泉声),甚至传递出触觉般的“冷”意,营造出幽深孤寂的禅境,高明的写景,常是视觉、听觉、嗅觉、触觉的协奏曲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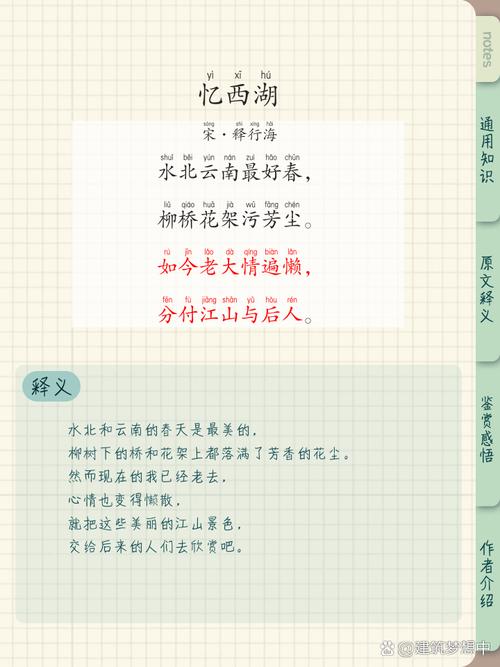
虚实相生的巧妙运用,实写眼前之景,虚写想象之景或象征之意,张继《枫桥夜泊》“月落乌啼霜满天,江枫渔火对愁眠”,前句实写秋夜凄冷之景,后句则由“江枫”、“渔火”引发羁旅之愁的虚写,实景触发虚情,情景浑然一体,又如屈原以“香草美人”象征高洁品格,景物已升华为一种精神符号。
再者是动静结合的辩证艺术,王安石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,一个“绿”字化静为动,赋予春风生命与创造力;而王籍“蝉噪林逾静,鸟鸣山更幽”,则以动衬静,用声响反衬出山林的空寂幽深,动静之间,景物的层次与韵味得以凸显。
意象的精选与组合,意象是承载了固定文化内涵与情感的景物形象,马致远的《天净沙·秋思》,“枯藤老树昏鸦,小桥流水人家,古道西风瘦马”,九个经典意象并置,无需赘言,一幅苍凉萧瑟的游子秋行图便跃然纸上,羁旅愁思力透纸背,中国诗歌经过漫长积淀,许多景物如明月(思乡)、杨柳(离别)、东篱(隐逸)等,已形成深厚的意象传统,鉴赏时需细细品味其文化密码。
融会贯通:在整体意境中把握景物
鉴赏景物形象的最终归宿,是领会其参与营造的诗歌整体意境,意境是情、景、理高度融合后产生的可感可悟、回味无穷的艺术空间,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简淡的景物与诗人超然物外的心境契合无间,共同构建出宁静恬淡、物我两忘的意境,传达了深刻的哲学思考。
杜甫的“星垂平野阔,月涌大江流”,雄浑的景物勾勒出天地壮阔之境,其中又蕴含着诗人漂泊无依的孤寂与生命的渺小感,意境宏阔而悲凉,鉴赏时,切忌将景物形象孤立拆解,应视其为意境生成的有机部分,感受其如何与情感、思想共鸣,最终形成打动人心的艺术整体。
古典诗歌中的景物形象,是自然在诗人心中投下的倒影,是情感淬炼而成的结晶,从出处背景中探寻其根源,从艺术手法中剖析其构成,最终在整体意境中领悟其神韵,这是一个由表及里、由象入意的审美过程,当我们学会这样去阅读,那些静止的文字便会重新焕发生机,带领我们穿越时空,与古人共赏一片风景,共感一份心绪,诗歌的生命,便在每一次用心的鉴赏中得以延续与丰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