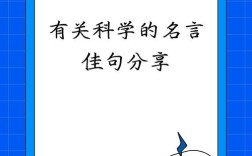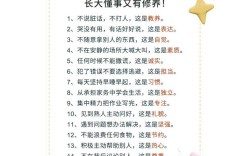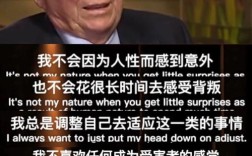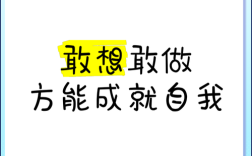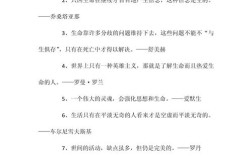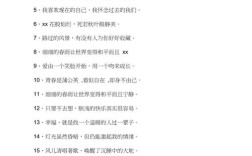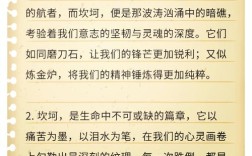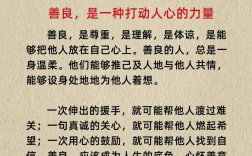梦境如雾,似真似幻,千百年来牵引着无数哲人与诗人的思绪,从庄周梦蝶到弗洛伊德解析,人类对梦的探索从未停歇,那些凝聚智慧结晶的梦之名言,恰似一扇扇窥探潜意识的窗扉,让我们循着智者的足迹,揭开这些箴言的重重帷幕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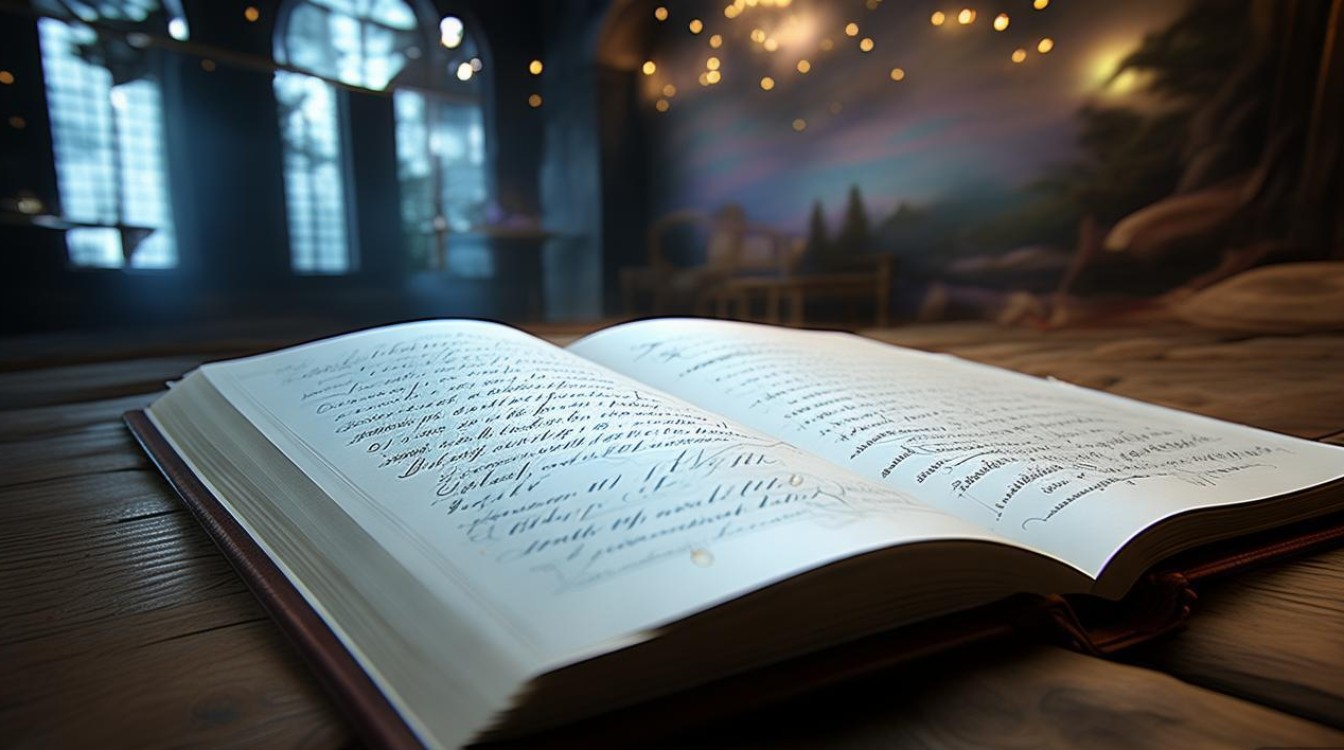
东方哲思:物我两忘的玄妙境界
“庄生晓梦迷蝴蝶,望帝春心托杜鹃。”李商隐在《锦瑟》中化用的典故,源自《庄子·齐物论》,战国时期,哲学家庄周以梦蝶之事提出惊人疑问:究竟是庄周梦见自己化为蝴蝶,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化为庄周?这种物我两忘的哲学思辨,打破了主体与客体的绝对界限,展现了中国古代哲学对现实与虚幻的深刻思考,运用此句时,可借以探讨自我认知的相对性,或形容某种浑然忘我的创作状态。
李白在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中挥毫:“我欲因之梦吴越,一夜飞度镜湖月。”这首名篇创作于天宝四年,诗人被排挤出京后漫游东鲁之际,诗中瑰丽的梦境,既是对权贵的蔑视,也是对自由的向往,引用此句,适宜表达对理想境界的追求,或衬托突破现实束缚的渴望。
西方探秘:潜意识深处的回响
莎士比亚在《暴风雨》中写下:“我们是梦境的材料,我们渺小的一生,在睡梦中圆满。”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巨匠,身处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英国,当时戏剧艺术繁荣,人文主义思潮涌动,这句话精妙地揭示了人生的短暂与虚幻,与同期汤显祖“人世之事,非人世所可尽”的东方智慧遥相呼应,在演讲或文章中引用,可增强对生命本质思考的深度。
弗洛伊德在《梦的解析》中提出:“梦是通往潜意识的光明大道。”这位精神分析学奠基人在19世纪末的维也纳,通过对精神病患者的临床观察,开创性地将梦视为欲望的伪装满足,此观点彻底改变了现代心理学对梦的理解,运用此名言时,可借以分析创作灵感来源,或解释日常生活中看似不合理的行为动机。
创作灵光:梦境滋养的艺术之花
斯蒂文森曾坦言:“小说《化身博士》的灵感来源于一场噩梦。”这位苏格兰作家在创作这部探讨人性双重性的作品时,正是梦境给了他关键启示,引用这个事例,能够生动说明梦境如何成为艺术创作的源泉。
北宋文豪苏轼在《江城子》中悲吟:“夜来幽梦忽还乡,小轩窗,正梳妆。”这首悼亡词创作于妻子王弗逝世十年后,梦中相见的场景饱含刻骨思念,使用这首词,最适合表达对逝去亲人的怀念,或渲染深沉的情感氛围。
智慧运用:名言的活用之道
理解名言的内涵固然重要,但恰当地运用更能让其焕发光彩,首先需要准确把握每句名言的原始语境与深层含义,比如使用庄子梦蝶的典故,就应了解其相对主义的哲学基础。
场景的匹配度至关重要,在探讨创新思维时,引用笛卡尔的“我思故我在”(其怀疑论思想与梦境密切相关)能增强说服力;而在分析心理现象时,弗洛伊德的观点则更为贴切。
巧妙融入行文有多种方式,可以开门见山,用“正如莎士比亚所言”引出观点;也可以先阐述己见,再以“这正印证了某某的名言”自然衔接,无论何种方式,都要确保名言与前后文气韵贯通。
创新性解读能赋予古老名言新的生命力,比如将“庄周梦蝶”与现代虚拟现实技术相联系,探讨真实与虚幻的当代意义,但这种创新必须建立在对原意的尊重之上。
文化视野:跨越时空的对话
不同文化对梦的解读各具特色,在古印度,《奥义书》认为梦是灵魂离开身体后的游历;在非洲某些部落,梦被视为与祖先交流的途径,这些多元视角丰富了我们对梦的理解。
将东西方梦论并置观察尤为有趣,庄子“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”的疑问,与笛卡尔“如何区分梦境与现实”的沉思,虽然时空远隔,却展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困惑。
随着脑科学的发展,我们对梦的认识不断深化,但无论科学如何解释梦的机制,这些凝聚人类智慧的名言警句,依然以其独特的文学美感和哲学深度,持续滋养着我们的精神世界。
站在个人角度,我认为这些关于梦的名言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依然鲜活,不仅因为其文学价值,更因为它们触动了人类共同的精神体验——对自我认知的探索、对现实界限的质疑、对创造力的追寻,在信息爆炸的今天,静心品味这些历经时间淬炼的智慧结晶,或许能帮助我们在这个虚实交织的时代,找到更清晰的自我的定位,每一句关于梦的箴言,都是先贤留给我们解读内心宇宙的密码,值得用心珍藏与品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