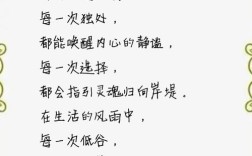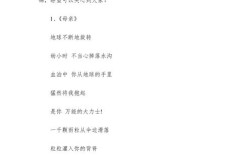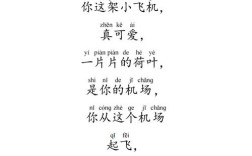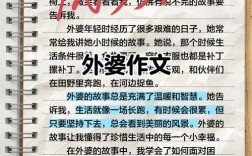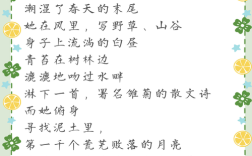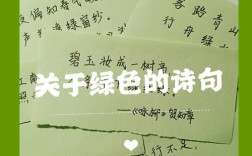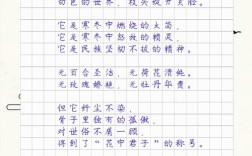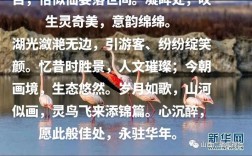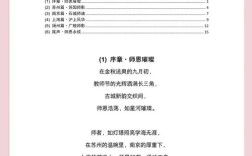春意悄然爬上枝头,细雨润湿泥土的气息总让人想起千年来的诗家吟咏,初春时节,那些藏在诗词里的生命律动,正等待我们以恰当的方式开启。

探源:诗词的根系与土壤
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初春意象,可追溯至《诗经》的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”,但真正使春景成为独立审美对象的,是南北朝诗人谢灵运,他的《登池上楼》“池塘生春草,园柳变鸣禽”,以自然观察取代道德比附,开创了纯粹的春日书写,这种转变与魏晋时期个性觉醒密切相关,诗人开始将内心微澜投射于自然变化。
唐代王维的《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》中“桃红复合宿雨,柳绿更带朝烟”,展现了盛唐诗人对色彩与光影的极致捕捉,这种细腻来自唐代园林文化的兴盛,诗人们得以在私人庭院中近距离观察物候变化,而宋代杨万里的《初春戏题山庄》“百舌强言事,黄鹂哑如吃”,则体现宋诗理趣——诗人从鸟鸣的断续中感悟到自然运行的微妙节奏。
解码:创作情境的深层理解
理解初春诗词需还原创作场景,李商隐《春雨》中“红楼隔雨相望冷,珠箔飘灯独自归”,凄迷春寒与诗人科举失意的境遇相互映照,若不了解唐代科举制度与文人命运的关系,就很难体会雨中遥望红楼的那份孤寂。
同样,杜甫《春夜喜雨》的“晓看红湿处,花重锦官城”,必须放在安史之乱后重建家园的历史背景下解读,这场滋润万物的春雨,对历经战乱的诗人而言是民生复苏的象征,这种将个人情感与时代命运交织的笔法,正是杜诗被誉为“诗史”的原因。
苏轼《减字木兰花·立春》中“春牛春杖,无限春风来海上”,则需结合宋代立春习俗来理解,当时的“鞭春牛”仪式蕴含着劝农重本的治国理念,词人通过民俗画面传递出对丰年的期盼,了解这些背景,诗词就不再是文字符号,而成为穿越时空的文化密码。
技法:古典笔法的现代启示
初春诗词的艺术成就,体现在多种创作手法的纯熟运用,温庭筠《菩萨蛮》的“江上柳如烟,雁飞残月天”,使用蒙太奇式意象组合,如烟柳丝与破晓雁阵构成视觉通感,这种手法在现代文学中仍具生命力,关键在于把握意象间的内在逻辑。
晏殊《浣溪沙》的“无可奈何花落去,似曾相识燕归来”,则示范了时空对照的艺术,落花与归燕形成消逝与循环的哲学对话,这种对立统一的手法能让作品产生持久的张力,当代创作者可借鉴这种思维,在对比中深化主题表达。
李清照《蝶恋花·上巳召亲族》的“随意杯盘虽草草,酒美梅酸,恰称人怀抱”,展示了细节描写的感染力,酸梅与美酒的味觉对比,巧妙传递出词人既欣慰又酸楚的复杂心绪,这种通过具象传递抽象情感的技巧,在任何时代的写作中都值得珍视。
活化:传统意象的当代运用
古典诗词的生命力在于持续被重新诠释,初春意象在现代语境中仍能焕发新彩,比如韩愈《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》的“天街小雨润如酥”,既可用来描述现代都市雨后的清新景致,也可隐喻文化滋养的细腻过程。
在具体运用时,建议把握两个原则:一是寻找古今情感的共鸣点,如王湾《次北固山下》的“海日生残夜,江春入旧年”,对新旧交替的描写适用于任何时代的变革期;二是进行意象转化,如将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的“绿”字活用为动词,描述新兴事物的萌发。
现代创作者不妨尝试将古典意境融入新题材,比如用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的理趣观察市场先机,以“二月春风似剪刀”的意象描述精微的创作过程,这种转化不是简单引用,而是让古典精神在当代土壤中重新生根。
初春诗词是中国人感受力的精密刻度,在柳条抽芽的瞬间,我们与唐代诗人看见的同一抹新绿相遇;在春雨飘洒的时刻,我们与宋代词人感受的同一份润泽重逢,这些文字之所以穿越千年仍生机勃勃,正因为它们记录的不是抽象的季节更替,而是具体生命对世界的细腻回应,当我们在自己的生活里发现那些被古诗精准描述过的瞬间,便完成了文化基因的激活——这不是对过去的怀旧,而是对永恒当下的确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