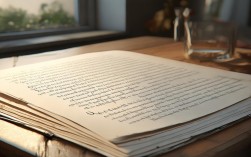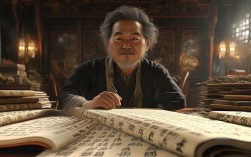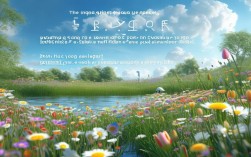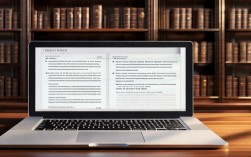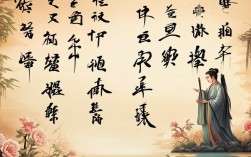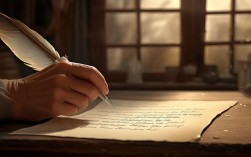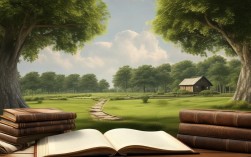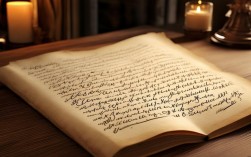紫罗兰,这种小花以其淡雅色彩和持久芬芳闻名,恰如诗歌在人类文明长河中的位置——不张扬却深刻,短暂绽放却留下永恒印记,诗歌作为语言艺术的精粹,承载着人类最细腻的情感与最深邃的思考,让我们一同走进这片紫罗兰般的诗歌花园,探寻其中的奥秘与美妙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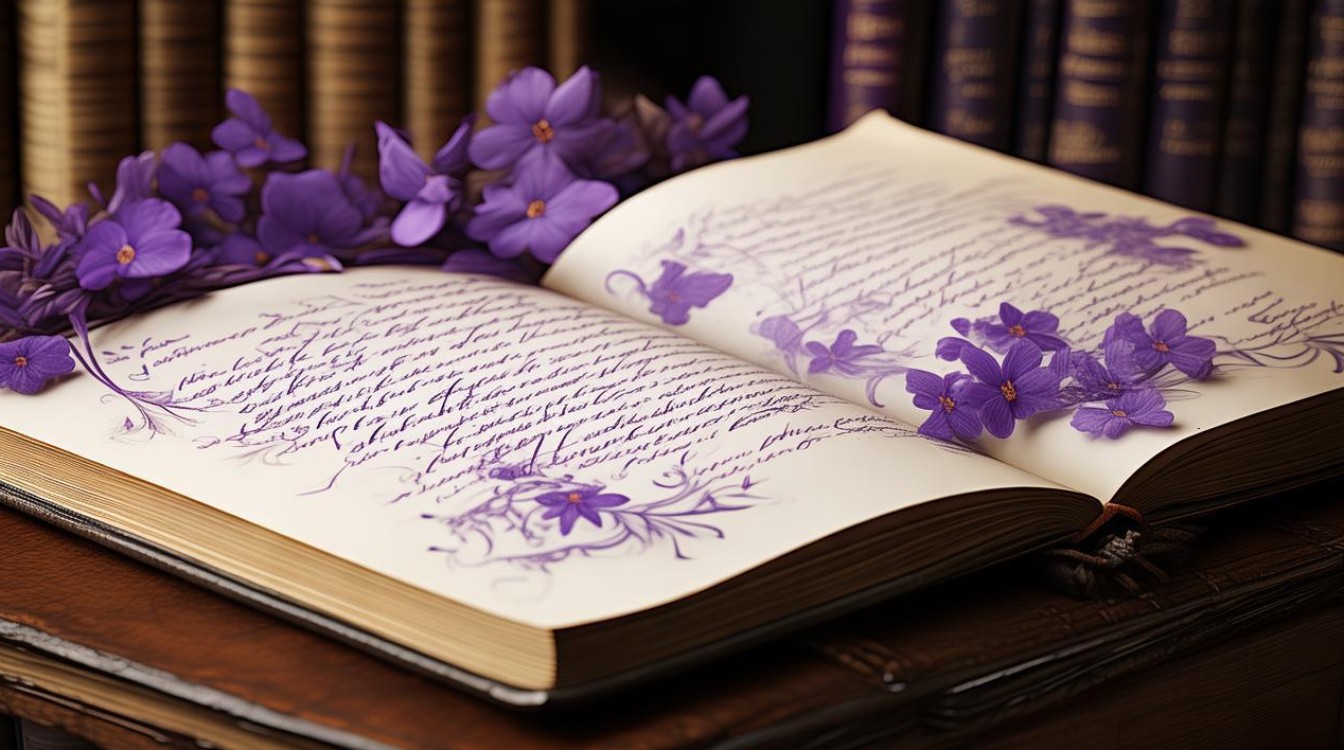
诗歌的源流与演变
中国诗歌的源头可追溯至《诗经》,这部收录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诗歌的总集,以其“赋比兴”手法奠定了中国诗歌的创作基础。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”不仅描绘自然景象,更寄托了深厚的情感,四言为主的句式,复沓的章法,形成了早期诗歌独特的韵律美。
战国时期,屈原开创了“楚辞”这一新诗体。《离骚》中“长太息以掩涕兮,哀民生之多艰”的咏叹,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,这种充满象征与神话色彩的创作方式,极大拓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。
至唐代,诗歌达到鼎盛,李白《将进酒》中“天生我材必有用,千金散尽还复来”的豪迈,杜甫《春望》里“国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”的沉痛,王维《山居秋暝》中“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”的空灵,共同构筑了唐诗丰富多彩的艺术世界,格律诗的成熟使得诗歌在形式与内容上实现完美统一。
宋词则在音乐性与抒情性上进一步发展,苏轼《水调歌头》的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,李清照《声声慢》的“寻寻觅觅,冷冷清清,凄凄惨惨戚戚”,或豪放或婉约,都将词这种体裁推向了艺术高峰。
诗歌创作的多元手法
意象是诗歌的基本构成单元,诗人通过意象将抽象情感具象化,如马致远《天净沙·秋思》中“枯藤老树昏鸦,小桥流水人家”,连续意象的叠加营造出浓郁的秋日愁绪。
象征手法赋予诗歌更深层的意蕴,闻一多《死水》中的“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,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”,表面写景,实则象征当时社会的沉闷与腐朽。
隐喻与拟人也是诗歌常用技巧,卞之琳《断章》中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,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”,通过视角转换,隐喻人与人之间相互关联的哲学思考。
现代诗歌在形式上更加自由,但内在韵律依然重要,徐志摩《再别康桥》中“轻轻的我走了,正如我轻轻的来”,通过词语重复与句式对称,创造出音乐般的节奏感。
诗歌的鉴赏与解读
理解诗歌需要结合作者生平与时代背景,李商隐的无题诗“相见时难别亦难,东风无力百花残”,若不了解晚唐的政治环境与诗人的个人经历,很难领会其中深意。
但诗歌解读不必拘泥于单一答案,北岛《回答》中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,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”,不同读者基于各自生活体验,会产生不同的理解与共鸣。
诵读是感受诗歌魅力的重要途径,古典诗词的平仄交错,现代诗歌的节奏变化,都需要通过朗读才能充分体会,在诵读中,文字转化为声音,诗歌的韵律美得以完整呈现。
诗歌在当代的价值
在信息爆炸的今天,诗歌似乎退居边缘,但其价值反而更加凸显,诗歌教会我们凝练表达,在海量信息中捕捉本质,三行诗、微诗歌等新形式的兴起,正是诗歌适应时代的创新。
诗歌创作也不再是文人专属,各类诗歌创作平台的涌现,让普通人也能通过诗歌表达情感,这种创作不仅是艺术实践,更是心灵疗愈的过程。
教育领域,诗歌培养着青少年的语言敏感性与想象力,从小学的古诗背诵到大学的诗歌创作课程,诗歌始终是美育的重要组成。
诗歌还成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,中国古典诗词的对外翻译,外国诗歌的引进,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与理解。
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诗歌如同城市中的一片绿地,让我们在忙碌间隙得以喘息与思考,它不需要宏大的主题,有时就是清晨的一缕阳光,夜晚的一声虫鸣,或是陌生人一个善意的微笑,这些细微处的感动,通过诗歌的表达,成为连接人心的纽带。
诗歌创作与欣赏能力的培养,需要持续的学习与实践,从理解基本格律到把握意象运用,从背诵经典到尝试创作,每一步都是与美对话的过程,不必急于求成,就像紫罗兰的绽放,需要时间的沉淀与耐心的等待。
当我们被某句诗触动时,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相遇,诗歌将个体体验升华为普遍情感,让我们在文字中找到共鸣与慰藉,这种独特的魅力,正是诗歌历经千年而不衰的原因。
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,诗歌依然是我们精神的栖息地,它记录着人类的喜怒哀乐,见证着文明的演进变迁,无论是古典诗词的典雅,还是现代诗歌的自由,都在向我们展示着语言的无限可能,或许,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生活中为诗歌留出一方天地,让这些美丽的文字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个阶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