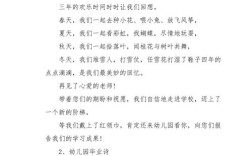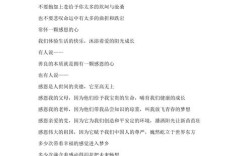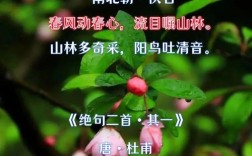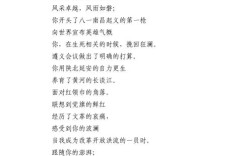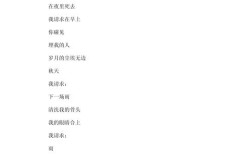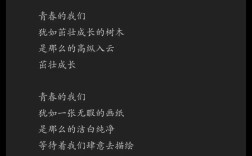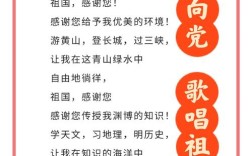诗歌是文化宝库中璀璨的明珠,它以凝练的语言承载着民族记忆与情感密码,从《诗经》的“关关雎鸠”到《离骚》的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,每首经典作品都是特定时代的文化切片,记录着先民的生活图景与精神追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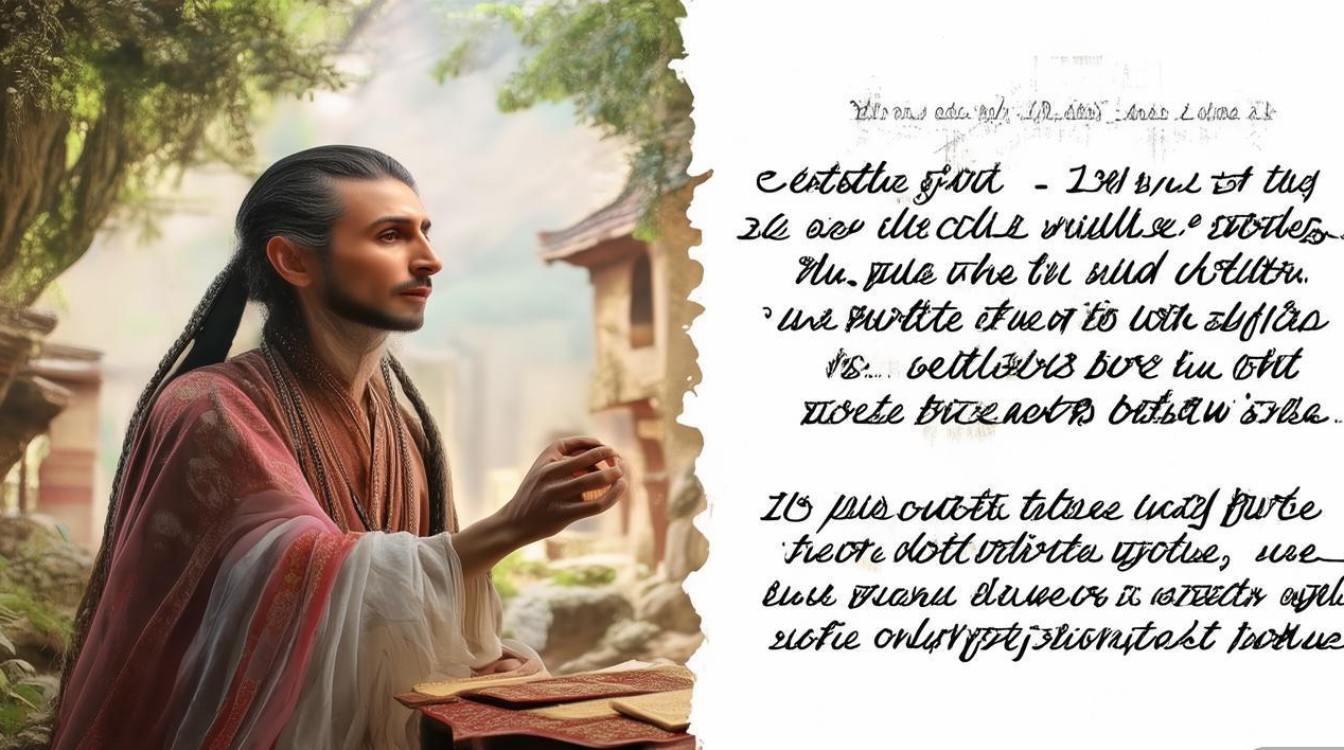
诗歌的源流与演变
中国诗歌的源头可追溯至西周初年的《诗经》,这部收录三百零五篇作品的诗歌总集,分为“风”“雅”“颂”三大类。“风”是各地民间歌谣,“雅”为贵族宴饮乐曲,“颂”则是宗庙祭祀乐章,这些作品通过“赋比兴”手法,构建起中国诗歌最基础的表现体系,屈原创作的《楚辞》开创了浪漫主义先河,九歌》改编自江南巫祭乐曲,《天问》以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展现对宇宙人生的思考。
唐代近体诗的成熟标志着诗歌形式的完善,李白《将进酒》中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”的磅礴气势,杜甫《春望》里“国破山河在”的沉痛慨叹,都通过严格的平仄对仗获得艺术升华,宋代词作突破诗律限制,苏轼《水调歌头》以“明月几时有”的设问开启哲思,李清照《声声慢》用“寻寻觅觅”的叠字传递孤寂,这种配合乐曲演唱的文体,展现出更自由的情感表达。
创作背景的深层解读
理解诗歌必须回归历史语境,陶渊明《饮酒》组诗创作于归隐时期,“采菊东篱下”的闲适背后,是诗人对官场生态的彻底失望,李商隐《锦瑟》中“庄生晓梦迷蝴蝶”的朦胧意象,需结合晚唐政治环境与诗人个人际遇才能领会,纳兰性德《木兰词》里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的感叹,折射出清代贵族文人的精神困境。
创作手法的艺术特征值得深入探讨,王维《山居秋暝》运用“空山新雨后”的视觉与触觉通感,构建出禅意空间,李贺《李凭箜篌引》借“女娲炼石补天处”的神话想象,将听觉转化为视觉形象,这些手法不仅增强表现力,更形成独特的审美范式。
诗歌的现代传承与活化
古典诗词在当代仍具有强大生命力,在文化教育领域,诗词教学应注重情境还原,通过吟诵感知声律之美,譬如《蒹葭》的叠章复沓营造出迷离意境,在文艺创作中,传统意象的现代化转译成效显著,某些影视作品将《诗经》婚恋诗改编为插曲,使古老文本焕发新机。
日常生活中的诗词运用更显智慧,传统节庆时,“海上生明月”成为中秋寄情的首选;文人雅集中,“曲水流觞”延续着兰亭雅集的精神;就连城市景观命名,也常取自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这类经典诗句,这种融入血脉的文化基因,正是诗歌传承的本质。
从个人修养角度,诗歌研读能提升语言感知力,反复揣摩白居易《琵琶行》的音乐描写,可训练通感联想能力;对比阅读苏轼《念奴娇》与辛弃疾《永遇乐》,能理解豪放词风的差异,这种训练不仅增强文学素养,更培养独特的思维方式。
在信息过载的当代社会,古典诗歌为现代人提供精神栖居地,当我们月夜低吟“江畔何人初见月”,其实是在进行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,这种文化血脉的延续,既需要学术研究的支撑,更依赖每个个体在生活实践中对诗意的守护与再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