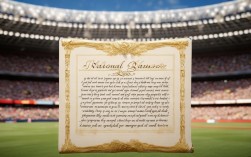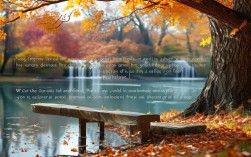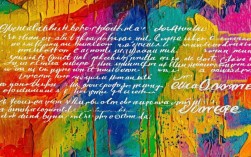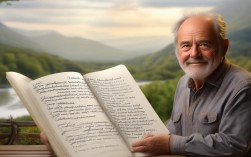下面我将从几个层面来详细阐述教坊与诗歌的关系。

什么是教坊?
我们需要明确“教坊”是什么。
- 定义:教坊是唐代设立在首都(长安、洛阳)的官方音乐机构,隶属于宫廷,它最初由唐玄宗李隆基在开元二年(公元714年)设立,其前身是太常寺下属的“内教坊”和“云韶府”。
- 功能:
- 培养乐伎:教坊是当时最高水平的音乐人才培养中心,它招募、训练和管理着大量的乐工、舞伎、歌伎,这些艺人技艺精湛,是宫廷宴享、祭祀、外交等场合的核心演艺力量。
- 创制与管理乐曲:教坊不仅表演,也负责创作和整理新的乐曲,许多风靡一时的“新声”或“时调”都出自教坊。
- 保存与传承:作为国家级的音乐机构,教坊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音乐、少数民族音乐和外来音乐(如胡乐),是当时音乐文化的集大成者。
教坊就是大唐的“中央音乐学院” + “国家大剧院” + “唱片公司”的结合体,是当时流行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中心。
教坊与诗歌的四种主要关系模式
教坊与诗歌的结合,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种形式中,每一种都代表了文学与音乐交融的不同深度和广度。
歌诗入乐:为诗歌谱曲,这是最高级的形式
这是两者关系中最核心、最理想的状态,即一首完整的、文辞优美的诗歌,被配上相应的曲调,成为一首可以歌唱的“歌诗”。
- 创作主体:通常是诗人自己谱曲,或由精通音律的宫廷乐师(如李龟年)为诗人的作品谱曲。
- 特点:
- 诗乐一体:诗歌的格律(平仄、押韵、句式)与音乐的旋律、节奏高度契合,诗歌的情感起伏与音乐的抑扬顿挫相得益彰。
- 文人参与度高:诗人不再是旁观者,而是直接参与了音乐作品的创作,这使得诗歌的艺术性得到了音乐性的升华。
- 著名例子:
- 王维的《渭城曲》(又名《送元二使安西》):这首诗被谱曲后,成为唐代最著名的“送别曲”,又称《阳关三叠》,因为诗中有“西出阳关无故人”一句,所以在演唱时需要反复咏唱三次,情感层层递进,感人至深,这几乎是一个完美的“诗乐合一”的典范。
- 李白的《清平调》三首:传说唐玄宗与杨贵妃在沉香亭观赏牡丹,命李翰林作新词,李白即席挥毫写下这三首绝句,后被乐师李龟年谱曲演唱,歌词华美,意境绝伦,音乐悠扬,完美烘托了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的盛唐气象。
- 王昌龄的《出塞二首》(“秦时明月汉时关”):这首被誉为“唐人七绝压卷之作”的诗歌,也被谱成乐府歌曲,广为传唱,其雄浑悲壮的气概通过音乐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。
声诗(乐府诗):先有曲调,后填歌词
这是另一种非常重要的结合形式,即先有一个固定的、流行的曲调(曲牌),诗人根据这个曲调的格律和意境来填写歌词。
- 创作主体:诗人或乐人。
- 特点:
- 依曲填词:诗人需要“戴着镣铐跳舞”,他的创作要受到已有曲调的限制,包括句式、字数、平仄等。
- 传播性强:因为曲调是现成的,所以新填的歌词很容易被传唱开来,这是诗歌走向大众化的重要途径。
- 著名例子:
- 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:这首长诗本身就是一首叙事性的“声诗”,诗中详细描绘了琵琶女弹奏的各种曲调(如《霓裳羽衣曲》、《六幺》),以及她高超的技艺,更重要的是,这首诗后来也被传唱,成为“声诗”的代表作,其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共鸣,通过音乐的力量传遍了天下。
- 刘禹锡的《竹枝词》:这是他学习巴楚民歌后创作的“声诗”,他模仿民歌的曲调,用白描的手法写下富有生活情趣和地方风情的诗句,语言清新,朗朗上口,非常适合传唱。
教坊曲名入诗: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意象
当很多教坊的曲调(如《菩萨蛮》、《忆秦娥》、《杨柳枝》等)流传日广后,它们的名字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,被诗人直接写入诗中,作为一种意象或典故来使用。
- 创作主体:诗人。
- 特点:
- 意象化:曲名不再仅仅指代一首歌,而是唤起听者对某种情感、场景或氛围的联想。
- 典故化:使用这些曲名,能体现出诗人的博学和与主流文化的亲近感。
- 著名例子:
- 温庭筠的《菩萨蛮》:“小山重叠金明灭,鬓云欲度香腮雪,懒起画蛾眉,弄妆梳洗迟,照花前后镜,花面交相映,新帖绣罗襦,双双金鹧鸪。”这首词的词牌《菩萨蛮》本身就是教坊曲名,整首词充满了华美、慵懒、闺怨的意境,与《菩萨蛮》这个曲调可能带来的婉约、缠绵的听感是高度契合的。
- 李白的名句:“箫声咽,秦娥梦断秦楼月,秦楼月,年年柳色,灞陵伤别。” 这首词牌《忆秦娥》也是教坊曲名,开篇的“箫声咽”直接将音乐意象引入,奠定了全词凄婉悲壮的基调。
描写教坊生活:诗歌成为记录教坊的“影像”
许多诗人,特别是那些与教坊艺人交往密切的诗人,会直接以教坊、乐伎的生活为题材进行创作,这些诗歌为我们了解教坊内部的真实面貌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
- 创作主体:诗人,尤其是那些与乐伎有交往的诗人,如白居易、元稹、张祜等。
- 特点:
- 现实主义涉及乐伎的技艺、辛酸、悲欢离合,以及教坊的奢华与残酷。
- 人文关怀:这些诗歌往往流露出对底层艺人命运的真切同情。
- 著名例子:
- 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:这是最典型的例子,诗人不仅描绘了琵琶女高超的演奏技艺(“大弦嘈嘈如急雨,小弦切切如私语”),更通过她的自述,揭示了“门前冷落鞍马稀,老大嫁作商人妇”的悲惨命运,发出了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千古感叹。
- 张祜的《观杭州教坊献乐》:“斜排柱阁新声发,尽选娉婷六么花,看取最先翻调处,合头声处断琵琶。” 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教坊排练新曲的场景,充满了现场感。
关系总结:相互成就,共同铸就盛唐风华
- 诗歌为教坊注入灵魂:优秀的诗歌为教坊的乐曲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优美的文学形式,没有诗歌,教坊的音乐可能只是技巧的堆砌,缺乏打动人心的力量,王维、李白等人的杰作,让教坊的乐曲得以流传千古。
- 教坊为诗歌插上翅膀:音乐赋予了诗歌无与伦比的传播力,一首诗,一旦被谱上曲,就能通过歌伎的演唱,在宫廷、市井、酒楼之间广泛流传,其影响力远超单纯的文本阅读,可以说,音乐是唐诗走向大众、走向不朽的催化剂。
- 共同塑造了时代审美:教坊与诗歌的结合,共同塑造了盛唐雍容华贵、开放包容、激情澎湃的时代审美,无论是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的华丽,还是“西出阳关无故人”的苍凉,抑或是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悲悯,都通过诗乐合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