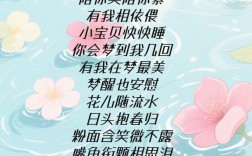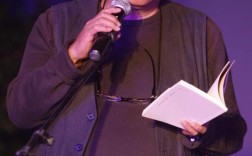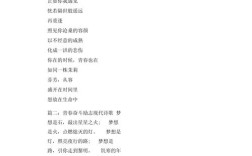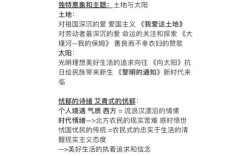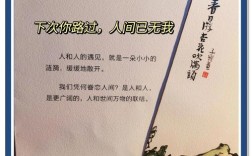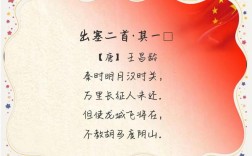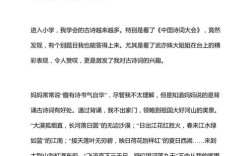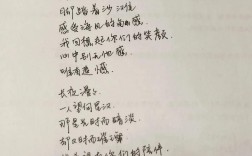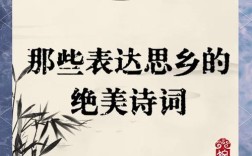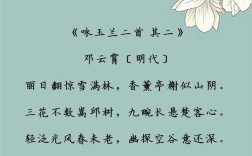诗歌,是人类情感与智慧的凝练表达,当它与“财富”这一永恒主题相遇,便催生出无数动人心魄的篇章,这些作品不仅是文学瑰宝,更是穿越时空的财富哲学,以其独特的韵律和意象,向我们诉说着关于拥有、失去、创造与传承的深邃思考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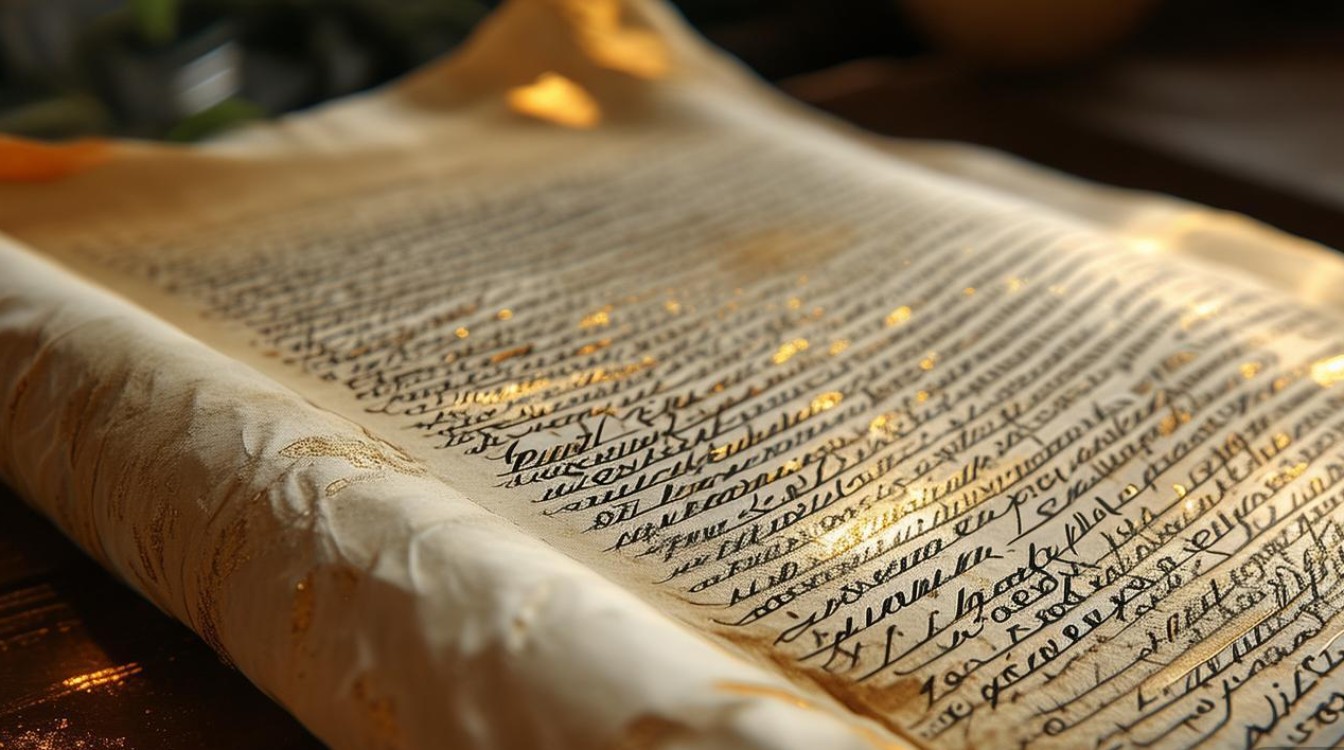
古典诗词中的财富观:超越物质的智慧
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浩瀚海洋中,诗人对财富的态度往往是复杂而辩证的,充满了东方智慧。
唐代诗人李白在《将进酒》中豪迈宣言:“天生我材必有用,千金散尽还复来。”这种对金钱的洒脱态度,展现的是对自身价值的绝对自信,财富在这里不是囤积的对象,而是实现人生豪情的工具,他的“千金散尽”不是挥霍,而是对生命能量的释放与信任。
与李白的豪放形成对比,晋代陶渊明则提供了另一种财富范式。《归去来兮辞》中“富贵非吾愿,帝乡不可期”的告白,以及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闲适,描绘了一种精神富足胜于物质积累的生活理想,对他而言,真正的财富是心灵的自主与安宁,是摆脱外在束缚后获得的内在自由。
杜甫的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则以尖锐的笔触揭示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,这句诗不仅是对现实的批判,更蕴含着儒家知识分子对财富伦理的深刻思考——财富应当承载社会责任,而非仅仅满足个人私欲。
这些古典诗人通过他们的作品,为我们构建了多元的财富认知:它可以是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,可以是精神自由的象征,更应当是社会责任的外化。
西方诗歌的财富隐喻:灵魂的货币
在西方诗歌传统中,财富同样是一个被反复书写的主题,常常被赋予深刻的象征意义。
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人莎士比亚在其十四行诗中,将爱与友谊视为最珍贵的财富,在第29首十四行诗中,诗人起初哀叹自己的命运多舛,羡慕他人的才华与际遇,但想到爱人的存在,心境便瞬间转变:“想起你的爱,便是财富如泉涌,我不屑与帝王交换处境。”这里的财富已经完全从物质层面升华到了情感与精神层面。
美国诗人艾米莉·狄金森则用她特有的隐晦笔法,将财富内化为一种灵魂状态,她在一首诗中写道:“财富,是我无法携带的东西/它不会在我的口袋里安息/但它会与我一起攀登天堂/在我死后,与我同坐。”她对财富的理解超越了世俗层面,指向了灵魂的永恒价值。
而沃尔特·惠特曼在《自我之歌》中歌唱的是一种更为宏大的财富观:“我辽阔广大,我包罗万象。”对他而言,真正的财富是拥抱整个宇宙的能力,是与万物相连的体验,这种将自我融入世界的慷慨,是对财富最诗意的扩展。
财富诗歌的创作手法与鉴赏
理解财富主题的诗歌,需要把握几种关键的创作手法。
意象的运用是核心,诗歌中的“黄金”、“珠宝”往往不只是物质财富的象征,更可能代表精神价值、爱情或智慧,而“乞丐”、“空虚”等意象则常用来反衬真正的富足,解读诗歌时,需要透过表层意象,探求其深层寓意。
对比手法在财富诗歌中尤为常见,诗人常将物质富裕与精神贫乏、外在拥有与内在空虚并置,通过强烈反差引导读者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财富,李白的“千金散尽”与“天生我材”的对比,正是这种手法的典范。
隐喻和象征让财富诗歌获得多义性,当诗人谈论“宝藏”、“珍珠”时,他们可能指向知识、爱情、信仰或任何他们认为珍贵的事物,这种语言的模糊性正是诗歌魅力所在,它邀请读者参与意义的共创。
在现代生活中运用财富诗歌的智慧
这些关于财富的诗歌不是尘封的古董,它们对当代人的财富观与生活方式有着切实的指导意义。
当我们陷入对物质财富的焦虑追逐时,陶渊明的诗句提醒我们审视:是否在追逐中迷失了更重要的东西?他的田园理想在当代或许难以完全复制,但其核心——对简单、自主生活的向往——依然能帮助我们平衡现实压力。
当我们在商业社会中经历挫折,怀疑自我价值时,李白的“千金散尽还复来”传递的是一种基于能力的自信,这种自信不是盲目自大,而是对自己创造价值的坚定信念,是面对市场波动时的心理锚点。
而当我们获得财富积累时,杜甫的社会关怀提醒我们思考财富的责任,现代社会的财富观越来越强调共享与循环,这与古典诗歌中的财富伦理不谋而合。
将财富诗歌融入日常生活,可以是通过晨间阅读一首诗来设定一天的情感基调;可以是在面对财务决策时,回想相关诗句以获得更深层的思考维度;也可以是在教育下一代时,用这些诗歌传递超越物质的价值观。
财富的诗歌最终告诉我们:真正的富足是一种内外和谐的状态,是创造与分享的能力,是与世界建立有意义连接的自由,它不在于拥有多少,而在于成为什么,每一首关于财富的诗歌都是一面镜子,映照出我们与财富最真实的关系,引导我们在物质与精神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点,在这个意义上,诗歌本身就成了最珍贵的财富——它无法被剥夺,却能无限增值;它不占据物理空间,却能拓展心灵的疆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