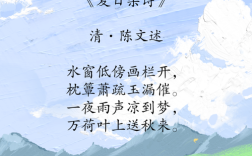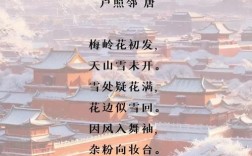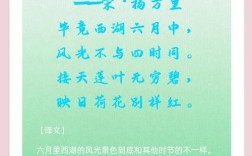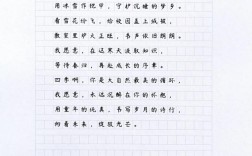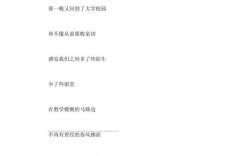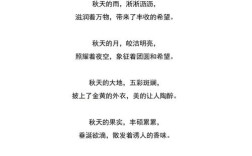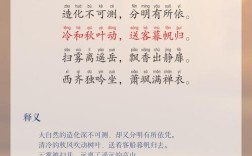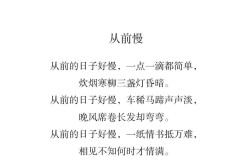诗歌,作为语言艺术的精粹形式,以凝练的节奏与意象传递着跨越时空的情感与哲思,从《诗经》的“关关雎鸠”到《神曲》的地狱巡游,从李白的飞瀑豪情到艾略特的荒原低语,这种文学形态始终是人类精神的精密刻度,理解诗歌需从五个维度展开:源流考据、作者心路、创作情境、鉴赏方法与艺术技法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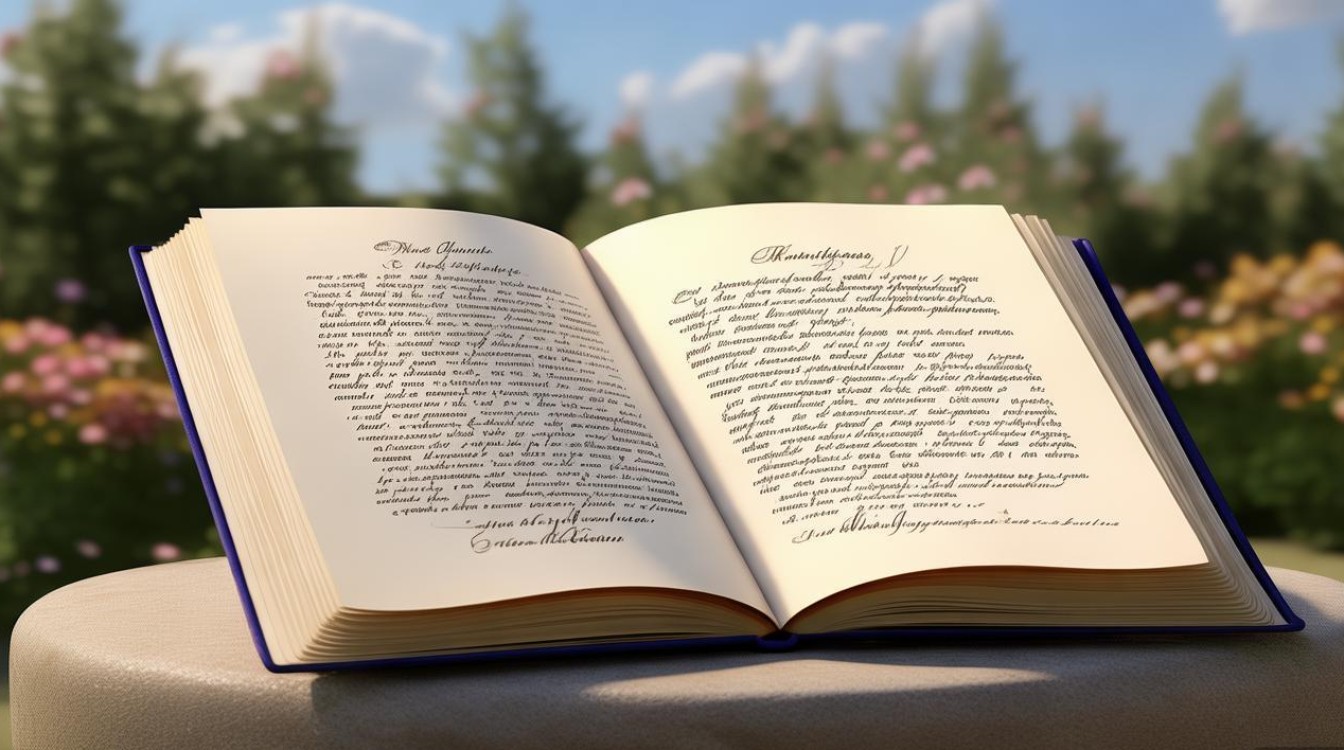
源流脉络:诗歌的文明印记 中国诗歌的源头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《诗经》与《楚辞》。《诗经》收录西周至春秋中叶的三百零五篇作品,分风、雅、颂三类,国风”源自十五诸侯国的民间歌谣,“雅”为贵族宴饮乐章,“颂”则是宗庙祭祀乐歌,这种早期分类已显现诗歌的社会功能:民间情感载体(风)、礼仪规范媒介(雅)与精神信仰依托(颂),屈原创作的《离骚》开创楚辞体,以香草美人意象构筑的象征体系,将个人命运与政治理想交织,形成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。
西方诗歌的演进则呈现不同轨迹,古希腊的《荷马史诗》以六步格律记载特洛伊战争,开创叙事诗传统,文艺复兴时期,彼得拉克的十四行诗将爱情主题精细化,莎士比亚则使这一形式成为情感解剖的利器,现代主义诗歌打破传统格律,如庞德《在地铁站》仅用两行“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/湿漉漉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”,通过意象叠加实现瞬间感知的传递。
诗人图谱:创作主体的精神坐标 诗人的创作往往与其生命轨迹紧密相连,杜甫历经安史之乱,在《春望》中写下“国破山河在,城春草木深”,将个人悲怆升华为时代见证,王维晚年隐居辋川,其《鹿柴》“空山不见人,但闻人语响”展现禅意与画境的交融,这种创作主体与作品的互文关系,在西方诗歌中同样显著,艾米莉·狄金森终身隐居,却在“我居住在可能性里”中构建浩瀚的内心宇宙,诗人通过文字建立的生命坐标,使诗歌成为穿越时间的精神容器。
创作情境:文本生成的历史现场 诗歌的诞生常与特定历史语境相关,建安七子的慷慨悲歌,折射出汉末动荡的社会现实;南宋陆游《示儿》的“王师北定中原日”,凝聚着中原未复的遗恨,了解创作背景如同掌握解锁诗意的密钥:不清楚晚唐政局,难以体会李商隐“夕阳无限好”的深沉喟叹;忽略英国工业革命背景,则无法理解华兹华斯对自然的虔诚礼赞。
现代诗的创作情境更趋复杂,北岛的《回答》诞生于历史转折期,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”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宣言,这类文本既是美学创造,也是时代的精神档案,要求读者具备历史视野与人文关怀的双重解读能力。
鉴赏方法:进入诗境的多元路径 诗歌鉴赏需调动多重感知,基础层面应把握韵律节奏,中国古典诗歌的平仄交错、西方商籁体的音步排列,皆构成音乐性骨架,进阶解读需捕捉意象组合,如马致远《天净沙》中“枯藤老树昏鸦”的蒙太奇式铺陈,营造出苍凉意境,最高层次的鉴赏在于领悟诗歌的哲学维度,苏轼“人生如逆旅”的道家智慧,里尔克《杜伊诺哀歌》对存在的质询,均超越具体物象而直抵本质思考。
当代读者可借助互文阅读深化理解,将陶渊明《饮酒》与梭罗《瓦尔登湖》对照,发现不同文化中自然书写的共通性;比较李清照“寻寻觅觅”与普拉斯《拉扎勒斯女士》,可见女性书写中的生命痛感,这种跨文化对话能激活诗歌的当代意义。
艺术技法:诗歌建筑的秘密蓝图 诗歌技法的精妙运用决定其艺术高度,中国古典诗歌善用比兴,《诗经·氓》以“桑之未落,其叶沃若”喻女子青春,自然物象与情感状态巧妙契合,典故运用则构成文化密码,李商隐《锦瑟》化用庄生梦蝶、望帝啼鹃,营造出迷离意境,象征手法在现代诗中尤为突出,闻一多《死水》以腐臭水潭隐喻沉滞现实,实现批判意图的审美转换。
西方现代诗歌的创新技法同样值得关注,艾略特《荒原》采用神话原型重构现代生活,庞德倡导的意象主义要求直接处理事物,威廉斯《红色手推车》通过日常物象的聚焦,揭示“那么多取决于/一辆红色的手推车”的哲学启示,这些技法革新不断拓展诗歌的表现疆域。
真正优秀的诗歌如同精密仪器,既承载着个体生命的温度,又丈量着人类精神的广度,当读者与文本相遇的瞬间,千年前的月光会重新洒落,异国的溪流将在心中奔涌,这种通过语言达成的永恒对话,正是诗歌最珍贵的馈赠——它让我们在词句构筑的星空下,确认彼此为同路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