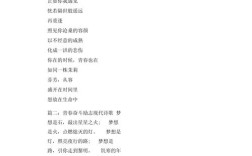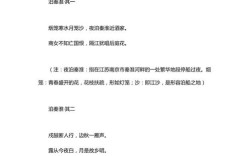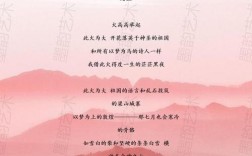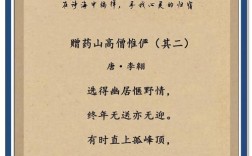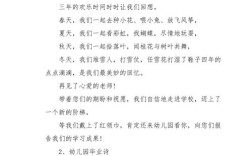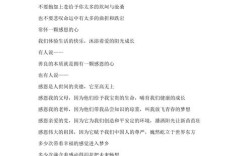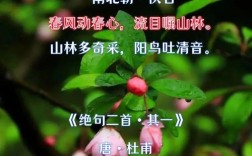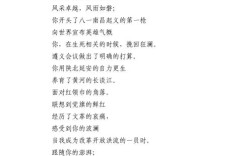诗歌作为人类情感与思想的凝练表达,在漫长文明中始终承载着和解与自省的功能,以诗歌为载体传递歉意,既能跨越直白语言的局限,又能在审美体验中完成情感疗愈,从《诗经》的"投我以木桃,报之以琼瑶"到现代诗中的忏悔独白,道歉诗歌始终在文学星空中闪烁着独特光芒。

古典诗坛的致歉美学 《诗经·小雅·采薇》中"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"的咏叹,表面描绘戍边将士的艰辛,深层却蕴含着对家人的愧疚之情,这种将歉意融入景物描写的手法,开创了中国道歉诗歌的意象传统,唐代白居易《琵琶行》中"同是天涯沦落人,相逢何必曾相识",看似抒发羁旅愁思,实则是诗人对自身仕途坎坷的释然,也是对亲友牵挂的隐性致歉。
宋代苏轼的《临江仙·夜饮东坡醒复醉》堪称道歉诗的典范。"长恨此身非我有,何时忘却营营"既是对自身处境的反思,亦包含对亲友的歉意,这种将哲学思考与情感表达融为一体的创作方式,使道歉超越个人层面,升华为对人类共同困境的观照。
西方诗歌的忏悔传统 但丁《神曲》中炼狱篇的忏悔诗章,通过象征手法展现灵魂的自我救赎,诗中"我的罪孽如荆棘缠绕"的意象,将抽象的道德歉疚转化为可感的视觉形象,英国诗人约翰·邓恩在《应急祷告》中写道:"每个逝者的钟声都是为我而鸣",这种将个人过错与人类命运相连的视角,拓展了道歉诗的哲学深度。
现代诗人艾略特在《荒原》中描绘的精神荒漠,本质上是对现代文明失落的集体致歉,诗中"这些碎片我用来支撑我的废墟"的隐喻,既是个体忏悔,也是时代诊断,开创了道歉诗歌的社会批判维度。
创作技巧的多维呈现 意象选择方面,李商隐"春蚕到死丝方尽"以蚕丝象征未尽的歉意,纳兰性德"人生若只如初见"以初见的美好反衬当下的遗憾,这些意象既承载情感,又保持审美距离,让接受者在诗意空间中自然领悟。
结构设计上,道歉诗常采用递进式抒情,如陆游《钗头凤》中"错、错、错"与"莫、莫、莫"的呼应,形成情感波澜;李清照《声声慢》通过"寻寻觅觅"到"点点滴滴"的铺陈,构建出完整的心理轨迹。
韵律安排亦需精心考量,古典诗词中平仄交替产生的节奏感,如杜甫"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"的工整对仗,能抚慰受创心灵,现代诗虽突破格律限制,但如徐志摩"轻轻的我走了"的柔缓语调,仍保持着道歉所需的庄重。
跨文化比较中的表达差异 日本俳句大师松尾芭蕉"古池や蛙飛びこむ水の音"以瞬间的禅意化解愧疚,体现东方文化中"不言而悟"的道歉智慧,波斯诗人鲁米"伤口是光进入你内心的地方"则将过错转化为心灵成长的契机,展现伊斯兰文化中的辩证思维。
这种文化差异在具体表达中尤为明显,汉语诗歌善用自然意象迂回表达,如王维"来日绮窗前,寒梅著花未"的含蓄问候;西方诗歌则倾向直抒胸臆,如雪莱"我倒在生命的荆棘上,我在流血"的强烈告白,但无论何种方式,核心都是通过诗性语言重建情感联结。
现代语境下的创新实践 当代诗歌创作中,道歉主题与新媒体形式正在融合,具象诗通过文字图形化传递歉意,如将"对不起"排列成破碎心的形状;跨媒介诗歌将音频、视觉元素纳入表达体系,创造立体的忏悔空间,这些创新既延续诗歌传统,又适应当代人的接受习惯。
在个人创作时,建议从具体情境出发寻找独特意象,若是友谊裂痕,可借用"裂镜"意象展开;若是亲情创伤,"断线风筝"的隐喻或许更为贴切,关键是要在共情基础上保持艺术真实,避免过度煽情或机械认错。
诗歌作为道歉载体,其价值不仅在于言语的精美,更在于创造了一个可供双方沉思的审美空间,在这个空间里,过错被转化为艺术经验,创伤通过韵律得到抚慰,而道歉本身也因诗性的照耀,从社交仪式升华为人类共通的情感教育,当我们在诗行间寻找恰当的表达时,实际上是在学习如何更真诚地面对他人,更深刻地理解自己。